走向开放多元的人类学
| 的是真的,你应该相信我”。
T:纪录片只能表现一定时间段的事件,而且只能表现表面的事物,你认为呢? J:这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如果一个人类学纪录片导演没有对一个地方进行长期的调查,可能会被认为拍出来的东西是不深刻的,所以还是要靠语言,通过被访者的话语、说话的表情、身体的姿势、说话的环境来洞察一些内在的东西,所以不能说纪录片就是表面的。可是有的时候,被访者回答访问者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因为环境限制,被访者可能会含糊其辞。 T:你刚刚提到“中国独立的纪录片导演”,这里所谓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J:“独立”指的是没有通过政府的审查。他们的影片通常是在国外、在电影节播放,在电视上一般是看不到的,不能公映。他们觉得如果要通过审查就必须改变原来想做的版本。 T:你打算怎么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做研究呢? J:我会和这些导演讨论影片创作的过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观察,通过自己的感官去感受,看看你可以从这个片子中学到什么。第二就是参加,我自己也是拍纪录片的,而且是拍人类学纪录片的,我自己就参与了这个过程。 T:你所做的实际上就是非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既有观察也有参与。当今人类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像美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您的作品也属于影视人类学的范畴,影视人类学作品比起人类学著作更直观,人们更易接受,像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就拥有数量惊人的观众。你当初选择拍摄人类学纪录片是否也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J:你说得对,这一方面与我爱好拍摄有关,另一方面也确实出于这种考虑。如果你写一篇文章,可能只有200个人会看,如果你拍一个纪录片,一个晚上就有200个人看。这其中的差别不言而喻,人类学要扩大影响力就必须考虑采用多元的研究方式和表现形式。当然,我也不是只拍纪录片,我还是要写论文,把自己的实践调查变成文字。 说到中国独立纪录片,我很喜欢一部叫做《天降》的片子,是在湖南拍摄的,影片说的是在湖南的一个小地方——绥宁县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残骸的理论落点,几十年来当地人民的生活一直不平静,谁都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有火箭残骸落到自己头上,这个地方的人很没有安全感。当地最优秀的一个女孩就是被这个残骸给砸死了。 T:这其中就有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意味。 J:还有一部记录片也特别有意思,叫做《北京的风很大》。它就是通过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来折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导演在街上随机地问路人这个问题,可是大家往往不会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他们会由北京的风聊到别的东西——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有跟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 T:由一个这么小的话题可以引发这么多内容真让人想不到。记录片似乎常常采用这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那在哪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呢? J:在宋庄可以看到,那是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宋庄有一个支持纪录片拍摄的基金会,有自己的影展、电影节,今年5月刚刚举办过一场,10月还有一场。独立纪录片的爱好者可以在那边看电影。 T:那你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吗? J:非常喜欢,尤其是他早期的电影,《站台》、《任逍遥》等。《站台》是他第一次使用数码技术,拍得很漂亮。他是一个很多元的导演,他广泛地借鉴其它国家的电影技巧,像台湾、法国、德国等,因此很成功。 T:你看过赫兹菲尔德教授的人类学纪录片Monti Moments: Men's Memories in the Heart of Romes和里科的《跑吧,中国》吗?你和他们拍摄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J:我看过Monti Moments: Men's Memories in the Heart of Romes,很遗憾没有看《跑吧,中国》,可是我知道他拍摄的方式是在街上随机地采访路人。我觉得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很少用采访这种形式来拍纪录片,我更喜欢安静地拍摄人们真实生活的情景,尽量不去打断他们,让生活自己说话。 T:《北方的那努克》被称为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可有人指出这部影片有明显造作的痕迹,比如因为室内光线不够好,弗拉哈迪就让他们将冰屋的屋顶截去,让那努克一家在冰天雪地里表演起床的场景;他们本早已习惯使用猎枪,却为了弗拉哈迪的所谓表现他们生活的原生态的要求,重新拾起父辈甚至是祖辈的捕猎手段。您怎么看待这些戏剧性的表演? J:那只能说是一种技术上的处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可是我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不会刻意要别人怎么样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表现,我就是拍摄他们最本真的生活场景。 T:我特别喜欢你的《拆·迁》,你是拍摄了许多画面再剪辑的吗? J:不是,我只在工地呆了3天,真正拍摄的时间只有21个小时。在我刚开始拍东西的时候,因为特别兴奋就拍很多,那样其实很难抓住重点。后来拍摄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几个星期就可以拍到足够的素材,我每天拍8、9个小时,可是我已经拍到了我需要的,没有必要拍很多。 T:你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在国际上屡次获奖,你可以介绍下它们获奖的情况并谈谈你获奖的原因吗? J:我2006年拍摄的《松花》在希腊一个电影节上获奖,后来又在波兰和美国的电影节获奖。《拆·迁》在巴黎的电影节上获奖。至于获奖的原因,评委说是因为我展示的不是中国的黑暗,没有拍他们在很辛苦地工作,在黯然神伤,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们生活中有情趣的一面,他们玩耍的情形,像《拆·迁》里玩极限运动的男孩子们,他们还会说很流利的英语。当然,这不是说我展现的都是那些光明的东西,我也有在影片中比较含蓄地揭露一些东西、呼吁一些改变。我也没有必要激烈地批判些什么,我是美国人,可我有强烈的平等意识。 T:最后,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你对人类学、纪录片的看法很有创造性,让我深受启发,相信对中国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人也是如此。祝你在中国学习、研究愉快! J:谢谢你!我也希望中国人类学可以走向世界,走向开放和多元! 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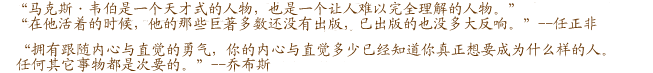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走向开放多元的人类学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