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多元的人类学
走向开放多元的人类学 【访谈背景】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超过一个世纪,而在近些年才获得真正的发展。在它日益成为“显学”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界要做的不仅是走向人民,更需要注目世界,理清一些基本的学科范畴,反思自己的研究方式,转变单一的传统调查形式,加强与国外人类学界的交流合作。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John Paul Sniadecki对当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误区有着犀利的见解,提倡一种开放多元的人类学研究模式,他本人也在坚持践行着一种新的研究理念——拍摄人类学纪录片。他在中国拍摄的《松花》(Songhua,2006)、《拆·迁》(Demolition,2007)、《四川记事》(Sichuan Triptych,2010)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连续获奖,他对人类学的理解和实践对中国人类学界在理清范畴及进一步发展上是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的。因此,在2010年5月底,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硕士生谭天佼就有关人类学的一些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关于中国 T:J.P.,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我知道你现在是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在清华大学学习,你可以介绍下你的教育背景吗? J:天佼,你好。我是美国人,祖上是波兰移民,到我这已经是第6代了,所以我也算得上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我本科学习的是哲学专业,硕士是在哈佛大学读的东亚系,现在在攻读哈佛大学人类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我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所以现在在清华大学学习,然后再回美国完成学位论文。 T:你对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能够说说你和中国结缘的过程吗? J:我第一次离开美国就是来中国,那是我20岁的时候,学校有一个挑选10名学生在大一暑假去中国学习东方哲学的项目。虽说是学中国哲学,但其实是给学生介绍中国,还有旅游的机会。因为我的专业是哲学,加上老师的推荐,我有幸成了这10名学生中的一员。我们被安排到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学习东方哲学。这听上去很奇怪,去一个理工学校学习哲学,这是因为我们学校和华东理工大学有合作项目,但实际上我也在那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学校和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关系,美国学生可以去上海、西安、北京,有时还有机会去四川、云南、西藏、山东。我在中国交到了许多朋友,中文也有了进步,对中国丰富的文化很有兴趣,所以有了进一步研究中国的打算。 T:来中国后和你想象中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吗 ? J:来之前我对中国没有什么概念,我只看过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还知道孔子。我是来了以后才慢慢了解这个国家的。 T:这让我想到里科(Rick Curnutt)拍的纪录片《跑吧,中国》(Run,China),很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百元人民币上面的头像是谁,有的说是胡志明,有的说是皇帝。大多数美国人只知道成龙、李连杰,只知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全部的了解。 J:情况确实如此。 T:你的《拆·迁》、《四川记事》都是在四川拍摄的,四川这个西南大省对你有着怎样特别的吸引力? J:四川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丰富性。那里有着多元的文化,有很多少数民族。最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一般,可是呆久了我发现它的节奏特别适合我。 T:你来到中国后觉得中国人有哪些性格特征?有人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时认为中国人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西方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J:我觉得这很难下一个定义,不过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了。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志在逐渐加强,也有明显的个人本位倾向,而西方人也并不是不重视家庭。可是,你说的这种区别确实是一种传统的差别,比如一个中国人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男子就会叫“大哥,你帮我……”,看到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大的妇女就说亲切地称呼她“大姐,你知道……”,这和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人不会这么称呼。而且中国人有自己的做人做事的规则,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话方式、行为规范。人和人的关系比较朦胧,这种朦胧有时是有好处的。 T: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成员,这样的称呼可以很快地拉近人与人的距离,这也是一种不见外的表现。那你了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情况吗? J:就我所知,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是研究人类学的专家,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也有一支研究人类学的优秀队伍,他们研究得比较早。可是总的来说,现在中国高校的人类学博士点还不多,人类学专业人才还不够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加强和国外人类学的交流沟通。 二、关于人类学 T: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人类学呢? J: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专业——东亚系,想学点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其实我选择人类学也是出于偶然,我从10岁就开始拍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后来发现我可以用我的摄像机来研究人类学,记录下人类生存的鲜活画面,这样可以很好地把我的专业和我的兴趣结合起来,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T:你在哈佛的导师之一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elle Hersfeld)说过人类学就是为那些在社会上不能发声的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我认为这说的就是为弱势群体说话,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J:我觉得这是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其实我拍的《拆·迁》就是这种性质,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们的生活展现出来,他们的笑和泪都是那样真实。可是我拍纪录片不完全都是抱着这个目的,像《松花》说的就是污染的问题。 T:你在哈佛的导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是医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你对这方面有过研究吗? J:很可惜,我没有做过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虽然他是我的导师。医学人类学怀疑西医的绝对权威,认为当今社会可能夸大了西医的影响,它是一种治病的方法,可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不一定要和我的导师研究一个方向,不过他的书很有意思,特别注重人的道德层面,在这一点我们是相同的。 J:对,我看了他的那本《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其中写到一个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他回国后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可是因为无法忘怀那场战争中自己的残暴行径郁郁而终。 T:是的,他无法原谅自己,他的道德感时刻在提醒着他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 T:凯博文教授2008年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学堂做过一个报告,介绍他在中国研究人类学的经历和感想,最后他说到:“从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就可以看出他所处的社会是怎样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J:其实这里的“身体状况”不仅仅是指人的健康情况,也包括一个人外在的一些姿势、表情、行为方式等,比如一个人的坐姿、走路的姿势、和别人说话时的表情等都可以透露出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 T:你是教徒吗?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吗? J:我不是教徒,我相信进化论。人自身的一些进化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可是有的观点,比如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就是无法证明的。可是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道理,我无法说它完全正确,可是必须承认它的影响很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流传很广。可是我反感后人利用进化论来证明其它的一些观点。反之,其实教徒也不一定就完全不相信进化论,我母亲就是天主教徒,她也相信进化论的一些部分,可她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开创的,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来自那个源头。 T: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进化论的理论,可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会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有人从医学角度指出人和猿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差异性,首先,人的血液是铁质的,猿的血液是铜质的;人有12对肋骨,猿只有10对肋骨。可我认为这不一定就是不可跨越的差异,在亿万年的进化长河中什么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J:对,所以我们要选择性地相信这个理论。现在它也是体质人类学一个激烈的争论点。 T:众所周知,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你做过田野调查吗? J:我做过,但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那种严格的田野调查。我是通过我的摄像机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记录一些对话来进行我自己的调查,可是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呆半年一年的经历,我一般是去世界上不同的地区调查。我认为田野调查中最重要的就是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参与观察),第一是观察,你要通过你的感官去了解。第二就是参与,你必须亲身参与实践。我现在也在做田野调查,去宋庄还有一些电影节调查,可是还没有完成,我的调查形式很灵活,没有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我现在研究的方向是中国独立的纪录片导演。 T:你了解中国的人类学家是怎么做田野调查的吗?田野工作 人类学田野调查 J: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或者说是社会人类学家,一般都选择和少数民族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文化。其实这里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研究对象被限定的问题,很多人类学家认为只有在不发达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才有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价值,其实在发达地区一样是存在研究价值的。美国的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就不一定都去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会研究主流的文化。因此,我觉得一个汉族的人类学家也可以研究汉族人是怎么过日子,不一定非要研究少数民族。 第二,许多人类学家拘泥于调查的形式。比如,很多人类学家在中国做研究都会选择去云南、青海等地呆很长一段时间,做一些所谓的“田野调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忽略了一个“权利”、“地位”的问题,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生活丰富快乐的人类学家去到一个偏远地区,但他和当地人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当地人的情况,无法感同身受。他在那住了一年后回到北京后写了一篇介绍当地人的文章,这样就显得有点奇怪、造作,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力。其实人类学家可以用一种更开放的方式去做研究,这样可能更有影响力。 T:我想这些田野调查的误区与人类学传统的研究方式有关,它最开始就是以研究异文化为主要方向的。一个汉族的人类学家去研究汉族人在中国的人类学家看来好像就不是那么纯粹的田野调查。而你选择用摄像机去记录人类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就这是一种新颖的开放的研究方式,我觉得是值得中国人类学家借鉴的。那你说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说的是一回事吗? J:不是。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比民族学出现得早。而且民族学只是限定了一个研究的范围,没有规定研究的方法,你可以从历史、政治等角度来研究民族学。而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是限定的。 T:你读过康拉德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吗?虽然他不是人类学家,可是被认为写出了伟大的人类学著作,以致现在有的人类学家说“人类学在等待它的康拉德”。另一方面,有的人类学家又呼吁人类学家在书写民族志的时候可以采用小说家的艺术技巧,更多地进行主观想象,以便更好地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你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J:我读过这本小说,有的时候民族志和小说的关系确实很难把握,这也说明了人类学的一个特点,它总是喜欢挑战自己,推翻一些已经稳定的观念,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之所以难以把握二者的关系就是在于它们实际上都是主观的,我认为其实人类学家书写的民族志本质上就是主观的,他们把自己所看到的用自己的语言有选择性地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主观书写的过程。我认为所有的书写其实都是主观的。因此可以说,人类学家在书写民族志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小说家的创作手法。 三、关于纪录片 T:你认为文本都是主观的产物,那你拍摄纪录片是不是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主观性? J:也不能说纪录片就是绝对客观的,只是它具有多样性,包含着各种意义,不同的观众可以看出不同的内涵。纪录片的缺点就是太朦胧,可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民族志的作家就不一样,他们有着这样的潜台词“我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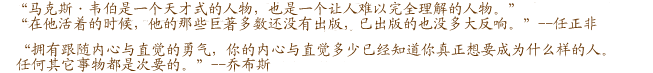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走向开放多元的人类学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