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考古学和史前史(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马克思与考古学和史前史(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和使用价值生产的著名分析强调了考古材料的重要性: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引用了这段话,对于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苏联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见1973年出版的阿尔齐霍夫斯基的《考古学》);而在西方考古学中,这段话则被结合到V·戈登·蔡尔德的一种创新的史前史的综合研究中(见“参考书目”③,第70——71页;④,第18页和26——27页)。可是,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古学和史前史方面知识不多,只是略胜于懂得从洞穴中发现石器这样的一般知识(见上面的引文),此外还了解到在近东不毛之地出土的遗迹所证明的在亚细亚社会中水利灌溉系统的重要性(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并参看亚细亚社会条目)。马克思意识到斯堪的那维亚人是考古的先驱者(参看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并注意到史前史的发现以及新近所确定的时代分期(如旧石器时代等),所以通过某种方式作出跟摩尔根提出的社会进化阶段相一致的解释(参看克拉德尔编辑的《马克思的人种学笔记》,1972年英文版,第425页)。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利用原始人和古希腊罗马史的人种学资料作为论证原始社会和国家起源的基本材料的做法,直到20世纪仍然如此。例如,在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一文中,几乎没有引证考古学的各种发现,有的话也只是用来论证一切人民都通过类似的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直线演进的观念(参看发展阶段条目)。普列汉诺夫写到;“我们关于‘原始人’的观念只是一种假设”,因为“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被发觉……距离人类不再去过纯动物的生活的时刻已经有非常久的经历了。”这样一段论述意味着考古学资料基本上没有能力再现更早时候的社会形式,并使人回想起约翰逊在一个世纪前说的著名格言:史前史是“关于无用事物的全部假设”。当然,社会进化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个主题,尤其是恩格斯的《家庭的起源》,但是,经过仔细的阅读可以发现,其中史前史几乎完全是靠人种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材料来编写的(根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所加的一个注释,该《宣言》的开头部分的一句话要订正为:“至今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这种缺乏考古学的论据的现象,如果仅仅根据主要的考古发现(如伊文思对克里特岛上青铜时代宫殿的发现)只是本世纪初才实现的这一点来解释的话,那是不正确和不充分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作品已经得到辨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遗址也已发掘出来,但是,由于与早期考古学的实践和结构有关的社会学原因,这些发现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当时,对考古遗物的研究没有构成人文科学教育的一部分,况且19世纪的考古学家基本上也并不关心这两位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感兴趣的社会进化问题。在欧洲,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刺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见“参考书目”⑨,第21页),而在近东,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人们想要证实《圣经》的历史准确性而得到推动。达尔文激发了对人类进化的兴趣,但是,早期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如加·德·莫尔蒂耶)所受到的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地质学的训练,因此他们希望史前史能够通过确定一个个连续的、可以跟地球史进行比较的时代,来揭开一种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考古学具有一种能够吸引有闲阶级成员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感召力(见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976年英文版,第113页),而古迹则容易被生活在农村而不易被生活在城市的人所发现。这样,跟哥德利埃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阶段的明显僵化所进行想当然的解释(见“参考书目”⑥)相反,在考古学实践和早期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宽广鸿沟,使人怀疑以后的考古学发现会对于修正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出现的论述或者对于改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普遍性的早期争端有重大的意义。 俄国革命以后,考古学在苏联第一次被纳入马克思主义传统。1919年,列宁创办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院成为该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研究机构。20年代后期,莫斯科的A.V.阿尔奇霍夫斯基和列宁格勒的V.I.拉夫多尼卡斯等年青考古学家,开始系统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于研究考古材料,他们坚持认为在这一基础上恢复早期社会的形式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参看马松著《苏联考古学理论观点的来源》一文,1980年俄文版)。在30年代,苏联的考古学家如彼·彼·叶菲缅科抛弃了三个时期(石器、青铜、铁器)体系,代之以把史前史社会划分为前氏族制(dorodovoe Obshchestvo)、部落制(rodovoe)、阶级形式,这种体系随后受到蔡尔德的批判(见“参考书目”④,第39页),并在50年代初被苏联考古学家斥为阶级理论的教条主义形式而被否定(见“参考书目”⑧,第12 —14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阶段划分仍然是重要的并且吸引了人们的主要的研究兴趣,虽然在诸如中国什么时候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这样一些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见“参考书目”②,第501页)。在中国,严格地从学术角度考虑来制定的考古研究方案,跟社会的或抢救的考古计划对比之下,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其主要的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考古研究所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于1950年建立的,然而有趣的是,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却一直分立出来,今天成为中国科学院(CAS)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所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西欧考古学在不断地发展。20世纪早期在欧洲所进行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特点都是以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史前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国外进行的大多数主要的文物发掘工作,其经费都是由对发现珍贵文物感兴趣的私人和博物馆提供的。例如在近东,在最大的城市遗址中心,大的公共建筑物——教堂和宫殿几乎是被发掘一空,然而却很少提供有关资助和修建这些建筑物的社会基础的资料。至于为了弄清楚整个社会的运行情况而对居民点模式所进行的研究,或对同类型的居民点(村庄、要塞、各专业生产地段等等)的分布状况所进行的分析,则到50年代早期才被G.威利作为一个考古程序引进到西方考古学中,这大约是在谢帕·托尔斯托夫在苏联的中亚使用这种方法的15年以后。 在西方,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概念跟考古学材料结合的主要学者是澳大利亚——英国的史前史学家V.戈登·蔡尔德(1892—1957年)。蔡尔德强烈地批判种族主义者滥用考古资料,并试图把社会形态跟技术革新联系起来。他认识到在生产力中的工业技术的发展或进步不能自动地引起社会的变革,并且正确地体会到,尽管考古学提供的东西是不完全的,但却构成了记录社会进化的原始资料,有助于在人种学的一般原理或类比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推测。 “自从人类从前人类中产生以来,人的需求就不是僵化的和固有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跟其他的任何事物一样。这种进化,也正如过程的其他方面一样,必须运用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加以探讨……因此,在进化的层次中任何技术手段和过程的序列,都不能从任何一般原理中演绎出来,而必须依靠考古学的材料。技术标准比政治和道德标准的唯一有利条件,是它能够更容易地从考古学材料中得到辨认”(见“参考书目”④,第21页)。 尽管有经验主义的偏见,但蔡尔德对史前史社会变革富有想象力的论述,创造了被共同接受的术语——新石器时代和城市革命。然而,他的著作还是有可批判之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偏重技术,而且由于其描述重点放在确定史前史的各自分立的阶段,而不重视解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水平进化和转变的过程。不幸的是,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中,这种只注重对抽象的阶段进行静止的描述的方法,仍然支配着一些明确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对这种情况的尖刻批判可参看“参考书目”⑩,第204页)。 当西方的考古学大体上是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发展的同时,史前史的发现——主要是通过蔡尔德的综合而传播——则对20世纪后半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讨论产生强烈的影响。例如,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争论中(见1962年出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人们经常引证考古学的论著去修正或改变传统上公认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序列,去完善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概念。史前史的发现大大延伸了人类生存的时间广度,展现出来的景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没有料想到的。人们追随蔡尔德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大部分历史是在近东野蛮人的边缘上度过的,而且欧洲是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的,因为这使它得以从古代近东所特有的停滞的、专制的管理形式中解放出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阶级社会最初是在史前史时期出现,换句话说,这样一种认识可能会第二次迫使人们对《共产党宣言》一开头的那句话进行修正。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解体,社会不平等的开端以及国家的起源,如今都成为需要参照考古学资料来处理的问题。 同时,在西方人类学中,一种进化论思想的重新抬头以及对文化现象的唯物主义——生态学解释的再思考(参看人类学条目),对考古学起了强烈的影响。美国的一些考古学家,例如泰勒,试图“发现在人工制品背后的印地安人”(即根据这些遗物形成的“来龙去脉”来再现当时的社会),而在本世纪60年代,一种“新考古学”则试图制订一种考古学标准来识别社会政治综合体(如团伙或酋长制)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些发展影响了一些考古学家,尤其是R.MCC.亚当斯(见“参考书目”①),他对各种不同地区进化顺序进行比较产生了兴趣,并且默认受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可是,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在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上所独立地得出的结论,虽然是以更为实证和精深的科学观点为依据,但却与本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考古学家所提倡的目标雷同(参看上面提到的马松的文章,第20页;以及“参考书目”⑧,第13页)。 再现社会的以往形态度并对它们如何发展和转变的本身作出解释,对当代考古学研究来说几乎是普遍的指导目标。近来在考古学方法上的进步,例如,采用精密仪器来确定年月的技术,广泛运用物理化学分析来确定人工制品出处的方法,采取标准手段来复原动植物材料以直接记录以往生物活动的方法,注重对地区性定居模式的确定方法,凡此种种,使得有可能采取蔡尔德所想象不到的方法来实现考古学的目标。今天,一些西方考古学家,如A.吉尔曼,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考古资料(见“参考书目”⑤)。但是,目前大多数有关人类演变的唯物主义的论述,仍然是缩小了社会的冲突,而把人类的史前史看作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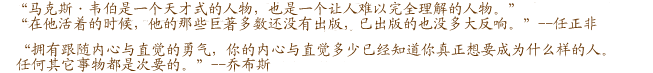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马克思与考古学和史前史(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y)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