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吐真言——一个游学者的准人类学随笔
作者 人类学
来源 人类学阅读
浏览
发布时间 11/01/01
| 酒后吐真言——一个游学者的准人类学随笔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网站 时间:2010-05-15 作者:石慎之 一 在当代中国,恐怕还没有哪位搞人类学的行家,倡言并实践过一种似乎“古已有之”的研究方法,即在酒席上或与人对饮的醉态中进行完全参与式的开放性访谈。 依我的管见,不少吃学术饭的人(刘小枫称之为“国朝学界”)习惯于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一种叫做“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围城中,并置身于标有“科学的研究方法”logo的工作服里。如所周知,无论是选择了还是追寻着怎样的生活,人们都会付出大致相当的代价。那些吃学术饭的人(扮乞丐做调查的王维平之类的人不在此列),他们从制度化的学院派意识中得到种种好处的同时,可能也会失去充满质野气息的民间思想资源的好处吧。 事实上是,他们向来都不稀罕这些具有创新因子的野东西。而我稀罕。带“野”字的汉语词汇及其意象群,我大都喜欢,比如田野调查、野史、野生动植物、野狐禅,还有野合等等。 可能有人以为只有像我这样不安分的外行人,才会主张和实践这种貌似荒诞可笑的访谈方法。可我认为这种深度访谈的方法,不仅非常有意义,它还可以让人得到意外的收获呢。 黄剑波曾写过一篇《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经验性宗教研究的问题及可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261-274),那是一篇内容让我赏心悦目,题目令我回味无穷的论文。文章平实敦厚,言近旨远,基本上看不出有跟读者拼脑子的主观故意。除开夹生的欧化长句的不爽因素,这样的文章我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下面要作一段中等规模的引用—— 在关于问卷与访谈那一节,他写道: “另一个影响人类学访谈的时间趋向更长的因素在于人类学家的一个假定,他们假定报道人对于外来者(研究者)具有天然的戒备。” 其实不消人类学家的那个假定,我据个人的田野调查经验就可证实,有的报道人不仅有戒备心理,还有基于戒备的迎合或游戏心理,也就是说,调查者认认真真记录的文字或音像资料,也许只是报道人的信口胡诌和伪装展现。 十年前我刚上大学时,就遭遇了某些让我哭笑不得的事——当我细读某些学者所写的有关我的民族(侗族)和我故乡民情风俗的著作时,感觉有些内容简直是天方夜谭。造成这种糟糕印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或是调查者的不力不察之咎,或是报道人的蓄意恶搞之失。那一段难忘的阅读经历,使我矢志向学之心锐减,并因此哼出“赝书未遂少年志”的牢骚来。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由诸如此类的种种历史碎片拼接而成的,我把它们概称为“不太幸福的生活”。 与此相似的“不太幸福的生活”,不仅随处可见,还可能随时让人置身其中。一年以前,在桂北的某个瑶族村寨(广西龙胜县和平乡大寨村),我又多次领教了报道人的那些密集的狡黠。所幸的是,辛苦的调查者不是我,而是中国南方某大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一群年轻学子。 值得强调的是,黄剑波在该文中也举有一个例子,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想真正进入一个文化,或者进入一个人的生活,就必须要花足够长的时间来保证这个关系的建立和进深。在此谨举一例。1998年我到四川大凉山地区做调查时,曾经就一个简单的问题向同一个人多次提问,然而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抵达这位彝族兄弟家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坐在火塘边上开始闲聊。我问他又几个孩子,他说‘一个’,并且说:‘只生一个好啊,养不起啊。’我问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他说是女孩,不过他说‘生男生女都一样嘛’。第二天那位介绍我到他家的当地干部离开村子回城了。晚上我再问他相同的问题,他说,‘还是得再生一个儿子’,并说‘女子留不住啊’。我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月,临走前的晚上我再次问他,他哈哈大笑着说,‘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接下来,他还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因此,尽管我个人完全赞同社会学家在访谈过程中所主张的‘所听即事实’的原则,因为这至少比‘猜想的事实’要更为可靠一些,而且若非如此,研究者就无法继续以下的分析和研究了。不过,作为人类学者,我主张研究者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使‘所听的’真正更为接近‘事实’。” 现在,作为一个游学者,我也想提一提我的意见:为了使社会学家“所听即事实”的主张不至于浅陋,也为了使人类学者“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意见得到落实,我觉得在做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实践我在开篇时提出的那种开放性访谈是十分必要的。我把这种方法暂时命名为“酒后真言法”。 在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布控的氛围中,“酒后吐真言”的经验性结论显然是很可靠的,也就是说,当调查者和报道人都醉得恰到好处的时候,访谈的内容才会更逼近事实。这实质上也正是一种碎片式(fragment)的假设—验证取向。不过我想认真说明一下,并不是所有调查者或报道人都适合使用酒后真言法。想要持之以恒地实践这一方法的调查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酒量够大,并且能够把握分寸,会恰到好处地进行提问; 胆胆够大,并且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报道人也许会说到一些让人惊惧的个人往事; 有过一定的人类学知识训练。 谁要是具备以上的几点条件,谁就可以开始尝试这种有价值的访谈方法了。 二 下面我想汇报一下,在2005年的一个月朗星稀的秋夜里,在桂北大山里的一个寒气逼人的溪涧旁,我非常出色地使用了这一方法,而我的报道人是一位背井离乡多年的瑶族ta2 kou5(瑶语,国际音标,意为大哥)。 如所周知,一个以稻作文化为中心的村落社会的理想调查周期是一年(宽泛地说,几乎所有农业社会的理想调查周期都是如此)。就在这种古典理论假设的鼓动下,我以“游学者”的不明身份,在桂北山区的某个瑶族村寨里进行了“往来于他者于自我之间”的实践。这次为期将近一年的实践之所以不得善终,只能怪我分寸感不强——自知不胜酒力却又不能适可而止,经常醉得一塌糊涂,连命都快赔进去了,哪还有精力搞田野调查并持之以恒啊。 那少之又少的成功个案实在值得认真记录。为了使所记录的东西有fragment的效果,我选择了自己比较习惯的札记形式,内容如下: 所谓的“农忙时节”,其实多是名不副实的,桂北的金坑瑶寨也是如此。秋收之前,村里的年轻人除了发“gan1’ zi5 bao5”(西南官话桂柳话,记音,意为“干子宝”)赌博,经常无所事事。为了暂时性地阻断他们这种常伤和气的“淳朴民风”,我从赌场中拽出了几个双眼尚未熬红的弟兄,邀他们去福平包(海拔1916米的山,在山顶可以看到广西最高峰猫儿山)“抓生活”,准备弄点山蛙之类的野味回来改善改善。 我们带上了一套简陋的炊具以及足够吃上两天的粮食和酒,做好了在山上过夜的打算。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放浪形骸,凡是看到可以食用的野果,就一律摘采、美味共享。野生的中华猕猴桃我们都吃得快拉肚子了,最好吃的还是冬杨梅,可惜挂在枝头的熟透的果子已为数甚少,一地的落果让我踩得心痛。“牛卵睾”(方言音为“niu2 luan5 kao5”)好吃蛤是难弄到,它总是长在高高的藤蔓上,若不是偶有几枝缠附于大树可以攀而摘之,我们就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掉口水了。 稍感遗憾的是,由于没带相机,我没能很好地拍下一张竹叶青蛇的图片,与它擦身而过时,它那一身让人心跳的迷人艳绿,让我产生了回归夏天的瞬间幻觉。 在到达据说山蛙经常出没的溪涧之前,我们本以为会满载而归的,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早先都太过乐观了。下午我们从离山顶不远的小溪顺流而下,捕获的小鲵比山蛙还多。由于天色渐暗,我们只好择地安营,砍下些细竹枝做垫席,在溪流涨水时冲开的涧旁石滩上稍做休息之后,就分头忙活开了:砍柴拣柴,生火煮饭,找野菜,弄山蛙、小鲵…… 当天捕获的一大桶小鲵到底算不算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当时哪有条件查证,反正,那一顿晚饭我们吃得心里胃里都美滋滋的。 怎奈天公不作美,向来秋高气爽的晴好天气有了我们不预期的变化。到了夜间,牛毛细雨翩然飘洒,我们只好生了一大堆火,围着取暖聊天,主题不外乎“抓生活”和女人(或说女人和男人)。到夜深人困时,有人提议大家分组轮流值夜添柴。作为一个骨灰级的“昼伏夜出,十有余年”的哲学青年,我马上挺身而出,慨然应允通宵值班,而另一位哥子也答应陪我守夜。于是他就成了我的调查对象。 我和这位报道人边喝边聊,不仅相谈甚洽,而且歌声不断。当我们双方的醉意都恰到好处的时候,他对我就全无戒备了,于是访谈便进入到了高潮阶段——其时已是下半夜三四点钟,潺潺的溪流愈显清泠,他的山歌声就愈加高亢,浑然不顾那几个鼾声四起但又睡得并不舒坦的人是否会被他的内力震醒。在那种情形下,我习惯性地问起了他对鬼神的信仰程度(或说他个人的鬼神观念),我话音刚落,他醉红的脸在篝火的映照下顿时变得铁青,眼神也显得分外地惶恐不安起来,他激动地对我说,下午那会儿,我们之所以弄不到山蛙,是因为水里面有鬼在作祟。到了夜里,那鬼一直在不远处的水里盯着我们呢,因此他才持续不断地用山歌来呵斥那鬼魂(其实是给自己壮胆)。 接下来,他一边紧握着我的手,一边“嗵嗵”地击打着自己的心口,带着十二分的诚意,热泪盈眶地说,他的心里好苦啊(一直生活在恐惧不安的心理重压下),他亡命十多年,正是因为以前他年少时因故杀人,然后缚石沉尸于青狮潭水库。而这种处理事情的办法,据说在他家乡一带是“习得性”的,也就是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延绵不绝…… 听了他的那一番话,我十分的醉意顿时消了一半。 彼时彼刻,我真希望社会学家“所听即事实”的主张,只是谬种流传。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我还是有清醒判断的,只不过,通过这个具体的访谈个案,我还没有置换身份的急智,因而没有想去做个民间宋慈,因为那不是我当下力所能及的事。天下事儿总有些隐秘处。人生在世也难免生出些过失。除了侦探警察维稳专家之外,寻常百姓大体上知道人身或有过失而人心向善,彼时虽有过失但此时向善,就可以过生活和打交道了。 在现当代的中国,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冤魂太多了。就我个人的经历看,我早就不惮任意外的杀身之祸。1999年在北京朝阳区的警所里没有被虐打致死,2001年在广州的黄村我没有死于非命……从此就什么形式的明枪暗箭都能直面,因为这还是一个从非法乱法向有法善法转换之世。何祚庥院士不是也说过“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了吗?他这句话的“中国”之前还应该加上一个“何某今生所在的”时间状语吧。 那个晚上以后,当我用google earth软件查阅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时,每次看到青狮潭水库的一汪碧水,我心底就生出寒意。 宗教学、法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求真之眼和信仰、法律、道德的求善之手,或许都有各自无力触及无从把握的领域。所谓的“现实社会”(生活世界或经验世界)的走向,并不都是趋真至善的。我希望更好一点的情形大致如此: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力量(自然和社会实体,以及思想及其载体)可以各行其所是,并且相安无事,即便它们之间有了摩擦、碰撞和冲突,其结果也将会趋真至善。至于最好的情形,我实在没有好好想过。 现在,“往来于他者于自我之间”的学者想必是生口日繁了,而“往来于生者于死者之间”的通灵者何在? 为此,我忍不住违心地说一句唯心的话:我若能通灵,我一定会说:愿青狮潭底的亡魂们安息吧。 写于2006年5月8日。 补:后来才听旁人说,那位大哥,确曾因过失伤人致死服过刑,刑期好像只有3年,那是一桩葫芦案。刑满出狱十多年来,他没再回过自己的家乡。 |
<< 生活一中产,美好就失掉一位人类学家旅行的意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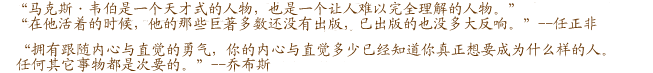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酒后吐真言——一个游学者的准人类学随笔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