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台湾人类学的田野
地方政治-台湾人类学的田野 黑道人类学 H是A村最具势力的黑道大哥。而我与A村初次结缘,则是廿年前的事了。当时该村正结束了一段轰动全国的反污染抗争,立场一向坚定的草根运动组织在两三个月之间掩旗息鼓,做为抗争焦点的工业建设于是在维安单位护驾下顺利过关。为何A村抗争会从持续数年的轰轰烈烈急转直下,最后草草收场呢?这个问题,从地方到中央、从社运界到学界一直有各种说法,其中最为信实但也最为隐晦的理由,便是地方黑道的态度转折。 究竟何为黑道?依A村的「常民分类体系」来说,地方黑道大致分为三类:上焉者是H这种以开赌场为生的「正派黑道」,这一类的内部也有分级,像H据说是「最高尚」的,他的收入从赌场、电玩、弹子店等等而来,但绝对不在自己村内开设这些场所,也拒绝别的黑道进入A村营业。中焉者则包括所谓「做黄的」,就是经营色情行业,以及卖毒贩毒者。而民间公认为最下等的黑道,则是靠恐吓店家摊贩、收保护费为生。各类黑道之间经常相互制衡,H不但抵挡外来赌场,也守护着该村的市场与夜市,让第三类黑道无法进来收取保护费。 据说从A村村民开始集结抗争,H就一直在幕后守护着这个草根运动。大哥自己不便出面更不能上台演说,但全力动用各种资源,除了出钱出物资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自己「面子」挡住外村黑道,不让任何兄弟溷溷到抗争现场来收取保护费,或藉机威胁勒索运动领袖。廿年前的台湾乡间有一句俗谚:「黑道怕警察,警察怕民代,民代怕黑道」,三环互动的恐怖平衡维繫着地方事务与派系权力的日常运作。抗争运动的兴起,除了挡住工程包商(通常与黑/警/民三环都关係密切)的财路之外,一群年轻人跳出来直接与大工厂对撞,更是绕过了地方上由民代、兄弟出面「乔事情」的惯性模式,不仅挑战国家权力,更扰动了地方的政治生态,若没有深厚的人情奥援,很容易沦为三环共同压制的敌手。而A村在抗争兴起的前几年,纵使在台北街头动作激烈,回到乡里却是一派和谐,靠的并不只是争取环境权的正当光环,更与外来社运团体的协助无关,从地方观点来看,民代与外围兄弟碍于大哥情面,没有动员恐吓带头抗争的年轻人们,恐怕是让抗争动能持续的更重要因素。 然而,这段乡野传奇在数年之后出现了无预警的转折:1980年代末期的扫黑行动中,H被管区提报,以违反社会秩序为由送交管训。少了大哥的加持,A村抗争阵营很快瓦解,运动中坚份子裡有的走避他乡,有的以酒浇愁,有的消沉以对。眼见这场抗争运动大势已去,大哥的小弟们据说在大哥示意之下,以避免造成村民更多伤害为由去「劝说」抗争领袖们停止行动,等待日后契机再起。兄弟们的「劝说」当然不会只是好言相劝,也包括规训行动:某某人的店面被砸、车胎被刺、家人被跟踨,都是村民当时盛传的耳语主题。 H的身份及角色,在A村固然是人尽皆知,但就像《哈利波特》裡的魔法人物对待那位「不可说」先生(He-who-must-not-be-named)的态度,村民从来不会/不敢向外人清楚指明H的姓名与所在,仅仅以「你知道谁」(You-know-who)模煳带过。即使某家大报已经针对H传奇做了专题报导,几位最熟的在地朋友面对我的询问时总是不置可否匆匆带过,于是H的真实面貌一直是我的一个田野谜团。直到廿年后,A村原先年轻气盛的兄弟们都已中年,也纷纷担任村邻长或社团主委等正式职务,我才首次有机会被正式引介与H认识,也才赫然发现,其实我老早就见过他了:那位常伴在C民代身边,长的瘦弱白晢,看起来像是民代随身助理的斯文男子,竟然就是H本尊。 样貌与我刻板印象中的黑道大哥相去甚远的H,廿年来逐渐「漂白」,目前担任A村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主委。虽然他拥有一辆黑色BMW,并在村外购置豪宅新居,但他习惯每天骑着脚踏车到村内旧家(一栋以铁皮及三合板钉成的简陋平房),这是他与宾客见面乔事情的私人办事处。在黑道大哥的逻辑中,首要原则是「诚信」,其次是「照顾自己人」,再来就是「敌我/是非分明」。针对廿年前的往事,H毫不隐瞒一一解答了我的疑惑:是的,A村当年的抗争的确是他去收尾的,原因正如前述,那场预知失败结局的抗争再拖下去,村民牺牲太大,不如先接受工厂提出的回馈条件,暂时休养生息等待他日再战。事实上,历经数个寒暑的抗争,A村当时民气已竭,鸣鼓收兵是许多人的想望,但只有H甘冒大不韪,出面终结这个在全国媒体闪耀着道德光环的抗争运动。他以「我先入地狱」的慨然语气说,「这件事只有我能来做。而既然这麽做了,我就等于是盖了印下去,不看到此事有个完满结束(意指污染源完全迁离),我眼睛不会闭上」。于是廿年后,在A村继起的反B工厂抗争中,H站到幕前,以他一贯的「大哥逻辑」,做着他认为最能照顾村民的举动,包括在屡次工安事件中以大哥式的气魄带头向工厂呛声、以主委身份动用公基金来补偿曾在廿年前街头受伤的村民家属、以及排除所有被他认定是站在工厂那边的人员及力量。 几个月前某某大学的学生曾经来到A村做问卷调查,研究主题是地方经济,但问卷中穿插了一些有关B工厂对当地经济贡献的题目,不幸惹怒了H。他说:「有店家跟我们抱怨,我们觉得不对劲,就跟随那个女生,当面跟她『沟通』。我说:『妳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怎麽可以帮污染工厂做这种调查?』」为了避免有更多店家「被骗」,H透过村庙广播系统向全村公告,建议村民若遇到某某大学的问卷调查员,不必对她们客气,直接赶出门即可。H叙述的轻描澹写,同样身为田野工作者的我却听的惊心动魄。我想像那位不到廿岁的大学女生,可能只是为了赚取一份工读金,或许再加上老师「参与社会」之类的理念鼓励,因此来到A村进行可能是人生中首次的社会科学调查,但迎接她们的并非台湾民间习有的善意相助,反而是一群父执辈年纪的中年男子的怒目相向,以及自村庙以降的全村联合排挤,这将对年轻女生造成什麽样的心理创伤呢?我实不忍想像。而在此同时,我也省察到自己与助理们这几年来在A村的田野为何能进行的如此顺利,为何田野中的「贵人」总是适时出现:儘管与H是最近才正式相识,但他必然早在廿年前的某时某刻,因为某种我并不完全清楚的原由,把我归类为「自己人」。这种自己人的身份带来研究的便利,却也造成长远发展的可能限制。 本文无意美化黑道,只想从H的故事指出一个台湾地方研究无可避讳的挑战:典型的台湾庄头组成原则,除了文献中熟悉的传统宗族与祭祀组织,以及较为现代的同业团体、志愿性社团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伏流,就是像H这样的黑道或灰道兄弟,他们依其所深信的人情义理所编织出的社会互动原则,深刻但隐晦地影响众多地方事务的走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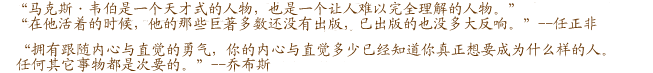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地方政治-台湾人类学的田野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