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者关于政治问题的一些困惑
有一点共识:良好的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成功民主的基石。无论我们未来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政治制度应该增加一些民主的成分,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 一个经济学者关于政治问题的一些困惑 有一次跟一位美国私募基金老板吃晚饭,提到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他说其实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建立民主制度的初衷并非发展经济,而是保障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该老板学业爱好为哲学)。这个观点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通常我们把中国和印度做对比,说中国经济发展更快,可能表明其政治体制更优越。这个判断起码有局限(当然印度的制度可能也没有很好地保护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这是题外话。) 即便我们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之一,集权也不一定是最优的体制。比如在前苏联时代,经济发展曾经令西方世界眼红,这正是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国家计划的经济制度的主要原因,可惜这些国家大都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前苏联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国家控制资源,大量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劳动比快速上升,但两者之间的可替代性却不断下降,最后导致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几乎为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经济就彻底崩溃了。我国在改革之前走过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 但后来的事情就变得有意思,前苏联崩溃以后,国家解体,俄罗斯迅速走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而中国则在文革结束以后开始逐步引进市场机制,但基本保持原由的政治体制。看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高下立见。曾经首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最近承认,看来俄罗斯根本不是一块金砖。其经济强劲还是疲软,几乎是单一地由石油价格决定的。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前景就要明朗得多。 但是否由此就可以说我们这样的政治机制就好呢?当然并非那么简单。我们历史上一向是实施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当然各个朝代集中的程度不一样),但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有效率,其实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需要明君。正因为有明君,才有了大唐盛世,才有了改革开放。如果遇到昏君,就有可能酿成人间惨剧。比如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大饥荒,但在朝鲜、前苏联和我国的几次大饥荒都主要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也就是说,集权制度下,明君是可遇不可求的。民主制度下,也并不能保证一定能选出明君,不过平均水平还可以,毕竟有个竞争机制。但最关键的还是有制约机制,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做好事也不能那么有效,干坏事也不容易。 无论我们未来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政治制度应该增加一些民主的成分,这一点应该是有共识的。曾经有一位高级官员非常坦诚地跟我说,其实我们高层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因为他们经常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面红耳赤。我认同高层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已经有提高,但老百姓的参与度很低,长期来说是个问题。我们有国人曾经笑话台湾民主,不光是议会打架,选出的又是一个腐败总统。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台湾在政治上的进步,民选总统出了问题,下来之后便坐了牢,这在集权国家很难想像,除非发生了革命,像埃及。 但是不是非民主不可或者非得走西方民主道路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可以拿香港做个例子。香港的政治制度不民主(当然五年以后就可以普选特首了),而且香港社会有其独特的问题,但如果政府效率与清廉在国际上应该还是领先的。我们曾经批评英国在一百年间没有在香港放开民主选举,但其实英国建立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一是监督,二是法律。媒体、立法会、反对党乃至普通市民以及廉政公署,都有权利监督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贪腐、腐败、浪费、不公等现象。记者问特首出差化了多少钱,特首就得答复。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制体系也保证正义能够得到伸张。 我们在改革期间,一直延续经济分权但政治集中的模式,长期来看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一旦中产阶层占据主导,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要求便会大幅提高。不过,我也很担心民主搞不好就变成民粹,也就是多数恐怖,俄罗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我们在农村推动民主化,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比如说民主是需要一定的教育基础的,农民一帮文盲,连啥是民主都弄不明白,如何让他们选好村长。确实也有不少实例,发现选了或者富人或者流氓。支持海选的人则说,让大家选,就能选出来,比任命的好,第一次选一个不好的,第二次就会学习进步。我是支持后一派观点的。 但重庆的事情又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主要是两点,第一,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前书记的政策实际是反经济规律的,巨额举债、劫富济贫是难以持续的;第二,但他在普通市民中的支持度非常高。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让重庆市民放开来民主选领导,谁会胜出?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如果以票数决定胜负的话,劫富济贫就是最好的策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归是穷人的数量要超过富人的数量。当然民主会成熟,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总是劫富济贫的经济政策。 那么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否成熟?应该很成熟了吧。这几年参与中美经济对话一个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美方代表(政府官员、学界人士与业界精英)和我们之间在大多数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但他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选举周期,总统选举、国会选举,一般就是两年一个周期。美方代表的说法往往就是:我们非常赞同你们的看法,但非常不幸的是,我们即将面对一场新的选举。也就是说这些代表往往因为选举带来的政治压力而放弃可能是理性同时也是最优的经济主张。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理解美国同行,但时间长了,就开始疑问:一,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最优的么?二,你们有选举,那凭什么我们也要连带着委曲求全? 当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摆脱了多数恐怖的阶段,但其新问题是华盛顿庞大的游说集团。曾经有一位美国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的成员主动找到我,告诉我当初保利集团在美国投资申请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请了洛杉矶最优秀的并购律师,但该律师并不了解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你想要让商务部和国会通过这个投资申请,必须找到华盛顿擅长这类业务的律师,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找谁。那位委员给了我大约十张可以提供帮助的华盛顿的律师的名片(现在看来这一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好在我没有转发那些名片)。所以,美国政治有点类似与内部人控制,谁有钱,谁就能够办成事情。这与民主何干? 欧债危机将西方民主制度的多数恐怖弊端表现得更加清楚:要想当选,就不能支持任何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改革。所以意大利的做法是临时任命蒙蒂做总理,而蒙蒂的最大优势还不是经济专家,二是他不参加普选,这样可以免受利益集团的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存在不存在中间道路呢? 比如我们过去一直追求经济市场化,但完全市场化就是最好的么?美国欧洲的危机表明即便是在发达经济也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就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困难是政府一上手就容易上瘾。另外,我们崇尚人权,但有一位挪威的学者曾经跟我说:西方的人权概念已经膨胀过度了,比如由原来的基本权利扩展到“不能被解雇”的权利等,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诸多问题,既超出我的专业范围,也没有成熟的结论,因此只能作为困惑提出来。另外,因为有些是敏感问题,所以一概谢绝媒体。(欢迎拍砖,但请维持学术讨论的氛围) 《一个经济学者关于政治问题的一些困惑》评论分享 拜读之后感觉黄老师已经非常专业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正在试图走着一条中间道路。但庞大的国家让这条路走的步履维艰。 呜呜呜,所以我今年呐喊的声音就大了很多啊,当那天我看到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都成了既得利益的一份子的时候,一种紧迫感迎面扑来! 呵呵,学经济学学的鄙视起来的啊 先收藏了。明天看。睡了,安 还是个讲逻辑、理义未丢的学者 说得非常好 政治制度有没有最优解呢?就美国而言,斯蒂格利茨说:过去是人人都可以有一个美国梦,现在是这个梦取决于你父母有多少钱。 我觉得。国家体制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坏与更坏之分。两害取其轻。相比下,民主制度还是更好些。另外,专制国家也是存在政治经济周期的。比如我们国家的“两会”或者党的代表大会。会上会提出新的发展的目标,新的动员,形成一轮新的经济扩张期。有一点共识:良好的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成功民主的基石。 这些问题真心比较浅啊!黄老师写的? 应该吧,黄老师一向这风格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还有更有趣更有范儿的老师么,哈哈哈哈哈。。。怀念那个时候的学习,讨厌意大利老师,讨厌全院都是意大利老师,不解释。 建立民主制度的初衷为保障个人权利,可民主制度的弊端带来的经济疲软保障得了个人权利么?反之,经济发展带来不了民主制度。所以,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几乎无相辅性。。 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不是普选,而是司法独立。 我是发现了姚前段时间是影评人,后来是球迷,现在成哲学家政治家了! 光有感想木有理论啊,他是要浅显易懂,让大家明白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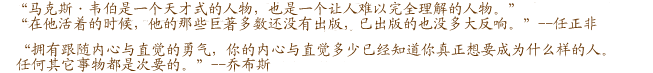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一个经济学者关于政治问题的一些困惑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