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人类学家那样走进历史
像人类学家那样走进历史 于是我想,是不是应该借鉴人类学家在土著部落搞田野调查的态度,即深入到土著人的生活里,讲他们的语言,参加他们的礼拜和狂欢,先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在他们的内部理解他们,然后再跳脱出来,在他们的外部思考他们。同样地,把历史当做一个悬隔在我们世界之外的世界,设想自己生活在一段历史当中,生活在一些虚虚实实的历史人物当中,讲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的必修课程,会写一手和他们一样的诗词和文章(甚至是八股文),参加他们的诗会、祭祀典礼和科举考试,先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在他们的内部来理解他们。 当然,这不太容易做到,八股文到现在我也写不好,只能做一个饮恨科场的可怜人,吟两句“五湖烟雨”的诗句来假装旷达罢了。但我的兴趣正是由此而转入了思想史,先去理解古人行为背后的观念,在思想脉络里来理解人的行为与社会的走向。 走进去,并不意味着“一入侯门深似海”,还要走出来才行。所谓走出来,就是用现代知识来思考古代社会。毕竟文明发展了,知识进步了,今天种种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于古人之上,让我们可以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享受一下比古人耳聪目明的乐趣。譬如对《老子》的无为之治与儒家礼治、法家法治之争,只要有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的基本素养,我们就会看得比古人清楚很多;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变法与守旧之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一言而定是非。 我这种态度引起过很多人的不满,他们大约是相信中医治不了外国人,西医也治不了中国人吧。虽然我对这些人的智力不愿做任何评价,但我尊重他们这种执着的信仰以及对传统文化远不止恰如其分的“温情与敬意”。 所谓“温情与敬意”,本是钱穆先生提出来的一项极受欢迎的主张,原话是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我承认这种态度有其十分的道德价值,但一不小心就容易堕入自觉或不自觉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偏见里去。钱穆先生自己在治学上就或多或少地流露出这一倾向,尽管他是一位令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伟大学者。 我自己的读书写作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既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万丈豪情,也缺少对修身养性、做人做事的实际关注,只纯然怀着一些好奇心罢了。就像一个人类学家进入一处遥远的土著社会,既不想使这里改变什么,也无意于以所见所得对现代社会提出任何的改良建议。 不过我自认为也算不得一个全然天性凉薄的人,我自己的“温情与敬意”更多地付与了一些更为抽象的东西,比如公正,比如自由。 我知道这是一副令人厌恶的嘴脸,就像阿凡达一样,这个卑鄙的怪物不但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更背叛了自己的星球和种族,恬不知耻地站在外星人的一边肆意践踏地球人的利益,甚至指挥外星人残忍地屠杀着地球同胞。这个反面角色被导演塑造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他不但把心交给了外星人,最后连身体都变成了外星人,显然没听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国古训。如果请阿凡达来写一部本国史,不知道他会不会写成一部“外国史”呢? 所幸阿凡达没有下笔,也所幸我的读者寥寥无几,站在热忱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我和许多人一样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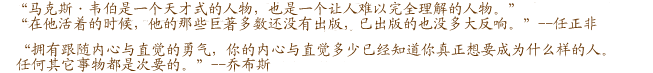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像人类学家那样走进历史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