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文化视野中的绝地天通思想
| o”。[11]在这则故事中,也有本教徒出现,但人数不是十个人,而是十二个人。这十二位本教徒是聂赤赞普的铁杆儿拥戴者,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他们的策划下演绎出聂赤赞普从天上沿木给来到人间的“拉日炯陀”神山,然后被拥戴为藏王赞普的。这十二位本教徒分别代表十二个部落,他们分别为:才米本(tshe-mi-bon)、象雄本(zhang-zhung-bon)、久拉本(cog-la-bon)、玛本(smar-bon)、塞本(se-bon)、拉本拉塞(lha-bon-lha-sras)等象雄六大本教师,以及赞氏劳与念(btsan-pa-lho-dang-gnyan)、曾氏琼与努(btsun-pa-khyung-rnubs)、念氏塞与波(gnyan-pse-dang-spo)等吐蕃六大世袭本等。[12]
第四,尽管“木给”与“建木”的传说在某些细节上略有区别,但从总体上讲,“木给”与“建木”的传说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古代的藏汉民族在崇尚天界,追求长生不死,相信肉体可以升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专家对其思想渊源和相关资料的考证也进一步说明了二者具有一致的可能性。如,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是先秦时代的古籍,是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对此卿希泰先生进一步指出,《山海经》的许多神话和宗教信仰的内容,都直接为后来的道教所吸取,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10]而天师道与藏古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1] 四、结语 古藏语木给(dmu-skas)是指通天之梯,古汉语建木是指通天之树,古汉语建木是古藏语木给的译音。木给与建木反映的是藏汉古文化视野中的早期原始的绝地天通思想。藏汉民族古文化中的这种绝地天通思想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分别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有专家认为,关于汉文化视野下的绝地天通思想,有专家从基本解释、传说、示例、发展阶段等四大方面做了阐释。 (一)基本解释 黄帝统治时代,民神杂糅,神可以自由的上天下地,而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即“昆仑山,黄帝所造”往来于天地之间。 (二)传说 蚩尤“带领众神和山精水怪与黄帝作对”之乱后,又殃及地上生民,使得人间强者凌弱,众者暴寡,酷刑泛滥,杀戮不止。后来,黄帝的继承者“颛顼”(zhuān xū)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一次大整顿。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 (三)示例 1.《尚书·孔氏传》:“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这就是说,“绝地天通”的关键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这是一种有序化、制度化的文化秩序重建,这为儒家的礼制提供了依据,也为法家提供了根基,为神仙家提供了神仙的体系,为远古先民的历史提供了思想治世的基础。 2.《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3.《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意谓使天地各得其所,人于其间建立固定的纲纪秩序。 (四)发展阶段 汉文化视野下绝地天通思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天地相通的原始思想阶段,意义世界由巫来管理。这是民众没有意义自主的阶段。二是人人都是巫的阶段。虽然意义的源泉开放了,意义自主了,但这又是意义世界的战争时期,意义与意义,信息与信息的冲突,正如《国语》中所说的“祸灾荐臻”。第三个阶段是绝地天通,政教合一阶段,以集团或阶级或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诉求,来赋予个人生命的意义,来垄断意义之源,来取消自主。第四个阶段是前面三个阶段的合题,既不是没有自主,没有权力地被赋予状态;也不是意义世界各自为政,意义与意义的战争状态,而是既有意义,又有区分;既自主,又和谐的一种状态。[13] 可见,上述这几个阶段在藏文化中既有雷同之处,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又有不尽相同的地方。比如,在古藏人的想象里“木给”无疑是人从物质世界通向意义世界的渠道。到了藏传佛教那里“法门”才是包括人在内的众生通向“涅槃法身”世界的唯一通道。藏传佛教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有望达到涅槃法身的境界。“法门”又分八万四千类,掌握这种学问和技巧者又分“法身”、“报身”、“应化身”等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藏族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这样或那样的教派以及各种活佛系统产生发展之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藏传佛教文化视野下绝地天通天人合一思想的一部演绎历史。 参考文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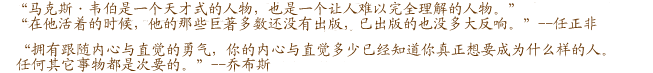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藏汉文化视野中的绝地天通思想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