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
| 的仪式的正确标记。在历史学家手下已经有文字证据的时候,甚至他也常常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较晚的历史。假定说,在学校里读过三十五卷李维的书。像汉尼拔(Hannibal)和准备跟安安条克(Antiochus)战争的誓词这类东西,毫无问题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来采用。但是,当谈到故事的时候,当时属于古罗马执政官之一的牛发出了可怕的话:“Roma, cave tibi!”——真是可笑。从教师方面来说,把这个故事作为单纯的李维的荒诞噱头跳过去,那是有缺陷的。他应当指出,大概历史学家是从关于怪事的某种官方报告中借用了它,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很好的历史证据,这种证据证明古代罗马人不只相信牛能说话,而且相信这类现象具有神示预兆的作用,相信这类可笑事件在罗马人中变成了民族的宗教和统治的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卜筮者们设法经常供给这类预兆以便于国家执政者的统治,或者,最低限度是使他们有可能来欺骗人民群众。因此,乍一看是最幼稚而荒谬的历史片断,却可能是文明史中的可靠的事实。
显然没有任何必要去创造证明古代世界生活的作品,这种创造实际上指的是给历史增加东西。古人传给我们的无论关于什么的语言和思想,如果都是确实可靠的,那么新时代的人自己就能够从中选出历史材料。例如,在《吠陀经》中集录的梵文赞歌,就可以作为歌唱它们的早期雅利安人每日生活的见证。因此,当献给风神的赞歌把风神说成是驾着有坚固轮子的车子,有精致的援绳和丝鞭的旅行者的时候,那么新时代的读者显然就会明白,创作这首赞歌的雅利安民族自己必定也是乘坐同样的车子。在那里面,光辉的神祗们为了美丽在胸前带着金练,肩上背着枪,腰间挎着短剑——这种神话形象提供了雅利安战士装束的真实画面。由此可见,这部史前赞歌的书一页页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雅利安人的古代宗法制的生活:他们带着畜群在广阔的牧场上游荡,或者关闭在冬季的茅舍里;田野上的耕作和庄稼的收割;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法权;对伟大的自然神——天神和地神、太阳神和霞光神、火神、水神和风神的崇拜,对于不生不灭的死者的极乐世界的热烈信仰;对布施的敬重和对正直的人的赞美。在古代波斯的圣典中——在《火救经》( Avesta)中——雅利安部族另一支的古代传统传到了现在,这一支信仰查拉图士特拉,是从婆罗门家族中分化出来的。两种宗教之间的深刻裂痕,显然在于查拉图士特拉的信徒们把婆罗门教的光明之神(deva)变成了恶魔(daeva)。他们认为婆罗门教徒们至今仍在实行的火葬是对圣火的亵读,他们对这种亵渎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早已使他们把死人交给食尸肉的野兽和鸟去食用,正像拜火教徒现时在自己的“寂静之塔”中所做的那样。在《火教经》的开头,提到了一个称为“雅利安子孙”(“Aryanseed”)的国家,作为由善神所创建的诸好国中第一的和最好的国家,后来,恶神就使它遭受到作十个月寒冬的诅咒。对气候的这种记述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古代波斯人相信他们的发源地是在奥科苏河和雅克萨尔特河的源泉附近、在中亚凄凉的斜坡上。在这些圣诗中,到处都有这些山地的、贫穷的牧马人和农民生活形象的影子,这些人跟现代腐化的波斯人和节俭的拜火教徒很少相似。他们埋头于耕种土地的繁重劳动之中,为的是让土地适于人的生存,具有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赞颂从土地中所体验到的享乐。当农民使用完了湿润的土壤,并对干涸的土壤进行灌溉的时候,于是土地就把丰饶带给用右手和左手、用左手和右手耕耘它的人: 种子一发芽,恶魔就低声指责;种子一发叶,恶魔就一声声地干咳;茎干一挺起,恶魔就又哭又嚎; 一长起粗壮的穗,恶魔就赶快逃跑。防避狼以保护羊圈和防备盗贼以保护村庄的恶狠狠的狗,对于人来说是如此需要,以致在这部书中包含有关于狗的特别严肃的条例——十分需要,如果狗不叫也不经心,就给它带上口套,并把它挂起来,这种处罚应当由给狗以坏食的人来执行;如果它”对富裕的户主也是这样——那书里进一步说——这同样是不好的。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干练的农场主的现实忠实画面,农场主们拟制出这样的规矩,是为使这些规矩由他们的子子孙孙重现出来,并传给未来的世纪。 这些粗野的雅利安人只能靠圣赞歌中的口头语言,来转达过去的回忆。较文明的民族则从早期起就开始记录有关当时事件的知识。最好的方法,就是想想这种最早的同时期的历史,这一点,看看在英国圣经考古学会指导下出版的《往事记》(Recordsof the Past)中埃及和亚述的文件译文就会明白。在那里面可以找到——例如,由伯奇(bircb)博士翻译的讲述乌纳(Una)远征的铭文,乌纳是特塔(Teta)王属下的侍从;在公元三千年前,卡尔纳克的殿堂墙壁上关于梅吉多( Megiddo)战役的说明;在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托特美斯三世(Thothmes IlI)在梅吉多击溃亚述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开辟了通往亚细亚内地的道路。我们读到,他作为一位国王,率领军队从加吉到比卡纳岸上的梅吉多南面,他在那里张开帐篷,对他的部队说;“快支起帐篷,我要在黎明时候去跟卑鄙的敌人战斗!”口令是:“坚决,坚决,警惕地守卫、守卫、守卫王国的帐幕!”在新月节日的早晨,国王在全体战士中间,乘着他那饰金的战车进入战斗;神阿门(Amen)是他的战士们的保护者,国王便战胜了敌人。战败者拜倒在他面前,抛掉马匹和战车,逃进堡垒;留在堡垒中的守军脱掉自己的衣服,用它把逃亡者从墙外拉过来。埃及人开始虐杀敌人,以致这些敌人都像鱼一样地并排躺下,之后,胜利者就进入了要塞梅吉多,国家领袖们带着贡品:金银、天青石和雪花膏石、盛着酒的器皿和畜群来到那里。细目清楚的俘获清单列举如下:生俘24O人,手(从死人身上切下的)83只,母马2041匹,岁口轻的191匹,金箱1只,“受轻视的”军队战车892辆,等等。题铭的最后一部分永远记下了常胜之王带给神阿门一拉(Ra)的丰盛贡物:田地和花园——用来补给其神殿的果实;鹅——用来填充神的湖泊,并且每天在日幕时让他得到两只肥禽,同样每天供给他面包和一杯啤酒。正如国王在他的碑铭中所提出的,他不自夸他做了些什么,也不说做得比事实上多,因为这会引起反驳。我们在这里看到,舆论的抑制力已经开始影响历史。当然,它并不强迫丝毫无误的真实,允许夸大民族的胜利和隐瞒失败,但是,即使是讲究虚荣的埃及,编年史也未必敢于记载毫无事实根据的事件。当转向巴比伦和亚述国的题铭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查尔德斯(Chaldees)的著名城市乌尔(现在称做穆黑尔Mugheir)的神殿的一块砖作为例子,在这块砖上有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辞句: 为神乌尔,其王贝尔之长子,乌鲁克(Urukh),雄强的人,勇猛的武士,乌尔(城)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建造了他的安乐的殿堂。 这里提到的苏美尔(Sumir)和阿卡德(Akkad),是古代达勒底的文明之地。各公元前十六世纪,汉穆拉比就已经征服了这些民族——这是一桩伟大的事件,因为由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的古代文化和宗教为作为征服者的亚述王国所吸收。这位巴比伦王在他的题铭之一中说:“贝尔的善意使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各族人民,从属于我的权力之下,我为他们从头开掘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人民的喜悦,供给人民以丰富之水的急流;我从头修复了它的两岸;建筑了新的防护墙;给苏美尔和阿卡德各族人民供应了不竭之水。” 借助当代人的这类记录,历史学家们现在能够核对古代皇帝的报道名单,拟定某种像从伟大的城市美姆菲斯和乌尔建立起埃及和巴比伦王朝的连续系列。我们可以指出,在最近几世纪记录在旧约《圣经》历史篇章中的以色列人的见证和传说,跟古代历史即古文献关于历史的见证相近。希伯来人的传说(《创世记》十一、十二)说,他们的祖先曾居住在乌尔的迎勒底附近和埃及,这就成了他们跟古代世界两个伟大民族有交往的证据。《出埃及记》(一、二)中提到以色列人曾被迫为法老王建造拉美西斯城,这说明他们的奴隶制属于第十九王朝中大拉美西斯二世时代,显然,大约在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左右,就形成了埃及和希伯来的年代记之间的相合点。在《历代记》中出现了后来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由于有与它们同代的其他国家的证据而十分著名。例如,所提到的希沙克( Shishak),他就是跟雷霍博姆(Rehoboam)作战并洗劫了神殿的埃及王(I,《列王纪》十六,25)。希罗多德的故事——亚述王森纳切利勃的军队由于老鼠咬断了兵士的弓而转为逃跑,似乎可能是《圣经》中关于森纳切利勃大灾大难的另一个故事(II,《列王纪》)十九的异文。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在这位全面审查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古代世界的图画,这位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好像对这古代世界了如指掌。历史之父——人们这样称呼他——不是作为本民族的年代记作者进行写作,而是抱着广泛的、对有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的人类学观点来写作的。最新的发现充分证实了他的报道,所以当他们像希罗多德那样细致地把传奇或传言跟他们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信赖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希罗多德讲述了关于冒充王者的奇怪故事,这个冒充王者是斯美尔迪斯,并且坐到波斯的王位上,直到他由于他那被割去的耳朵而被识破为止,大流士杀死了他。若干年前,波斯贝希斯坦附近的一面高高的峭壁上所刻的楔形文字题铭被破识了,它们原来正好是大流士王用三国语言所作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跟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故事相一致,这就足以证明希罗多德确实十分熟悉他那个时代之前整个世纪中波斯的事件过程。而且希罗多德的下述故事还能经受更好的验证,这个故事据他说是根据埃及的祭司们的口述记录下来的,是有关于他们两千年前的国王的。在他们的口授之下,他记录下了金字塔国国王——切奥普斯(Cheops)、切弗伦(Chephren)和米开里诺斯(kykerinos)的名字。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批评家们有时表示怀疑:这些国王是真实存在还是纯属凭空杜撰?但是当埃及象形文字丧失的意义被现代学者们重新考释出来的时候,他们读到了希腊历史家在当时听到过的那些名字。最古的历史证据能在长期丧失了意义的古文献中遇到这类的证明。苏基迪德说(六,54),彼西斯特拉特(小的)设立了两个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的铭文已经被雅典人损坏,但是在另一个上面(历史学家说)虽然文字不好辨认,现在还可以通读:“彼西斯特拉特(希彼亚斯的儿子)把自己执政的这个纪念碑放在得尔福的阿波罗神殿的门廊里。”这块带有题铭的石块的一部分, 1778年在伊里索斯附近的一庭院里找到,现存雅典博物馆中。下面这种研究家能够最好地了解这类文献赋予历史以何等生动的现实性,即这种研究家从自己的书本到不列颠博物馆,并在古代钱币中看到了生着羊角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头,他曾公然宣称为宙斯-阿蒙的儿子,而币中的这个头像就是他生活中的这一奇异插曲的纪念;或者,研究家会惊异地注意到那种金币——这种金币证明辛白林(Cymbeline)确实是铸造带有自名字的钱币的真正不列颠王。这个辛白林由于莎士比亚( ShaksPere)而闻名于现代。 这样看了早期历史材料之后,会发现这种历史是如此地有利于人的研究,我们就没有必要转到后来历史的陈腐基础上来。我们仍然要谈谈神话这个常常使历史学家们跌跤的绊脚石。不能把神话只看作是迷误和荒谬,相反,神话是人类智慧的有趣的产物。这是想象的历史,是关于任何时候也没发生过的事件的虚构故事。特别是导世纪写作的历史学家们,记录了关于真实事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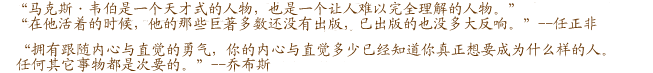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