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
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 [ E.B.泰勒] 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传说——诗歌——虚构中的事实——最古的叙事诗和书面作品——古代的记事和历史——神话——神话的解释——神话的传播 我们已经不大求助历史来证明人类生活的最早时期了。正如本书的第一章所指出的,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知道,最古的民族已经湮没而不为古代的民族所知道了。但是,不应当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历史已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此相反,现在有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好的证实手段证明其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借助像古代的文献和语言这样一些证据,再加上现代历史学家所发现的那许多极早的著作,来进行这一证明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过是需要从那些传说、诗歌和有关历史开始时期的书面证据中获得鲜明的概念。 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或多或少是由那些在文字出现之前从祖先那里靠记忆传下来的传说组成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不可能教导我们多方面地认识这类口头传说的价值,因为在文明世界里,传说是那样地不适用,而当时发生的事情又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在现代,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祖先早期时代的事件知道得极少。但是,文字还没有普及全球,还存在这样一些民族:这些民族的历史仅仅由祖先传下来的传说组成。例如,直到不久以前还不会书写的南太平洋岛民,是有知识的野蛮人,他们希望把关于既往时日的回忆传给后代,并在一两种情况下,这些回忆在他们之中可能受到检验,看来,记忆好像真的能够十分长久而忠实地保留历史知识。传教士惠特米(Whitmee)报道说,在罗图马岛上有一棵极古老的树,据传说,树下埋着一位著名领袖的石座。不久,这棵树被暴风拔出,树根下果真有提到的领袖石座,它避开人眼想必已埋藏了若干世纪。埃利斯群岛( Ellice Islands )上的土著们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在许多代之前从遥远的萨摩亚(Samoa)群岛的一个溪谷里来的,他们保留了一根古老的被虫腐蚀了的木棒,这根木棒的各部分由于用木块绑着才免于散掉。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言人手中握着它,作为有权发言的标志。这根木棒不久前曾经拿到萨摩亚群岛去,才知道它是由那里生长的树木制成的。同时,在所谈到的那个溪谷里的居民们中间,保留着这样的传说:在从前某个时候,从溪谷里出来一大群居民,他们到海上去探险,大都没有回来。在这些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传说中,最著名的是毛利人所传播的那些关于他们的祖先在新西兰定居的传说。他们说,在一场内战之后,他们的祖先从夏威夷群岛乘小船逃往外地,向东北航行;他们引用建设者和船队的名字来证明他们登岸的地点;他们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从乘小船到来以后各代领袖的名字,这样一共有十八代,或者从新来者占据这个岛那时起已有四百到五百年。虽然正如可预料到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有矛盾,但他们却用来作为一种文件,由于这种文件,土著们就根据他们祖先的权利占据着土地。他们的祖先是乘独木舟“鲛”(Arava)和“神的独眼”(Mati-atua)登陆的,而且未必能够怀疑,人们中间经常重复的这类家系所依据的是现有的事实;而这些人的土地所有权就决定于这些家系。但是,毛利人的这些传说有一半是由最简陋的传奇故事组成的。当一个小船的建造者砍倒一棵大树以便做小船骨架的时候,他第二天回到森林里发现,一夜之间树又立在原地了。当小船已经造成并放到海上的时候,魔法师留在岸边。但是小船到达新西兰,魔法师却像骑海豚的阿利翁(Orion)骑在海怪背上,比移居者早一步游过大洋到达那里,已经站在岸上了。新时代野蛮民族的这些传说,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埃及和希腊早期历史中真实的回忆和神话幻想相混合的十分真实的概念。根据传说,上述的历史是从当时甚至还没有文犊员在石板上刻下皇帝名字的遥远过去传下来的。 当传统用文字传下来时,特别是在诗人们赋予传说以诗的形式时,传统就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甚至现时在英国,某种突出事件变成了叙事诗歌在全国歌唱。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作为历史家的诗人的作用比起后来要大得多,许多古代的欧洲歌曲带有真正历史年鉴的印记。不列颠的古代歌曲常常包含着极为真实的历史。例如,其中有一支提到了伯特兰·杜·格斯克林(Bertrand du Guesclin)的头发像狮鬣,而在另一支里描述着,冉·德·蒙特福特(Jeanne-la-flamme)为了带剑和燃烧着的木头从亨尼朋(Hennebont)出发,去烧法国兵营,她把军事装备披挂了起来,这种装备经其他历史材料证明她是确实带过的。虽然诗人和吟游诗人保存着许多像刚才所援引的具体事件,但是他们对所报道的事实却没有历史家的良心感。由于希望感动听众或者迎合他们的心意,为了使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领袖的家族自豪感得到满足,歌手在领袖的大厅里歌唱时,他就将自己的歌曲带有真实的名字和事件,但是这样安排它们,就更使他的故事具有戏剧性,甚或是直接编造历史。伟大的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 Lied),是在勃艮第(Burgundy)开始的,那里有三个王掌握着莱茵河上沃尔姆斯的会议,他们的姊姊是美丽的克里米尔特( Kriemhilt),她的丈夫西夫里特( Sifrit)被哈根(Hagen)阴谋用枪刺杀在小河旁。之后,她就嫁给匈奴王阿提拉,而流血的故事就以她的复仇和死亡结束,留下了伯尔尼来的阿提拉和乔德利奇及在牺牲的战士身上哭泣的人们。在这里,地点和个人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可以编成叙事诗形式的历史,如果历史只凭这类传说就能写成的话。但是吉本的读者知道,实际上,阿提拉在乔德利奇诞生前两年就死去了。这首叙事诗只是一种传说的后来的异文,它的较早的形式是作为《佛尔松萨迪》而保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引用沃尔姆斯王宫,骑士比武,以及所有其余历史人名和地方情况,只是为了赋予故事以诗的性质和色彩。中世纪已经有了编年史,而这些编年史能够揭穿诗人们;如果诗人们在这时戒除了伪造历史的恶习,那么我们在那些还没有历史稽核所的时代的叙事诗中,怎样才能把事实和虚构区分开来呢?《伊利昂纪》和《奥德修记》可能包含着许多关于真实的人及其事业的回忆:或许某位阿伽门农事实上是在迈锡尼统治过;对特洛伊的包围也可能真正发生过——或许恰好正是在那个施利梅曼挖出了金杯和金项饰的土城周围。但是要从荷马的叙事诗中寻找出历史的真实来,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在荷马的叙事诗中,自然的事件和奇迹,就像在历史传奇中那样混杂在一起。要判断在某位歌手的口头上对各民族的编年史不偏不颇地保留到何种程度,极为困难,正如格拉德斯通先生在他的《荷马入门》(Primer of Homer)中所指出的,歌手把任何一个杰出的希腊领袖在神圣的战斗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特洛伊人杀死当成了常规。如果在古代诗歌中,除了关于历史事件的歪曲了的回忆之外,找不出任何东西,那么,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把诗歌完全弃置一旁,那将是最明智的事情。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诗歌是最全面而确切的认识文献之一。 虽然诗人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他所谈到的可能是历史。在各民族、国家和城市的名称中,诗人在我们面前无意地表现出社会及其居民,他们在当时如何。在《伊利昂纪》的第二部里,人和海船的名单是地中海海岸地图及海岸居民的概述。荷马了解埃及人,了解他们的田地灌溉及其医疗技术,了解由于自己的船舶而享盛名的脱尼基人及其绛红色的纺织品。卡德莫斯(Kadmos)这个名字是腓尼基语,意思是“东方的”,其实他的同伴们所建造的“七座门的”底比斯,证明他们对神秘数七报以崇敬,这种崇敬导源于巴比伦对七大行星的崇拜。诗人未必能想到,他所讲述的充满怪异现象的故事,其中有现实世界的情况,未来世纪的人们正是要重视这种关于现实生活的证据。抓住大公羊的肚皮或者动身往冥国到苍白的死人阴魂那里去的奥德修斯,是纯粹的神话。然而对波吕斐摩斯的描述,是为数不多的古代低级野蛮人风俗画面之一,而访问冥府,这是古代希腊宗教中人们所想象的精灵之阴惨的冥府生活的一章。对于生活和风俗的描写也是如此。诺西卡(Nausikaa)公主坐着两头骡子驾的大车,载着要洗的内衣到河边去。奥德修斯沿着航海的斐亚克人(phaiakians)的大街走着,对海港、坚固的墙壁和堡垒感到惊异,后来就迈过阿尔金诺(Alkinoos)宫殿的门槛,进去抱住王后阿瑞蒂(Arete)的膝盖;然后坐在灰烬中的炉灶上,直到国王想起雷神宙斯跟这位请求者很亲近而且很关心他的时候,才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到自己旁边儿子的辉煌座位上。随着黠智的奥德修斯的传奇性历险,我们看到,宛如在许多活动的模糊的画面上,古时的英雄们手中拿着枪,脚旁跟着快犬走着;在一座房子的进口大门旁边,他们丢掉衣服,进入浴室;又从那里出来,身上擦过油之后就到宴会上去。在宴会上,他们没有任何像盘碟或刀叉之类的细致器具,把烤肉和面包吃了个够;他们在平坦的林中草地上扔盘子消遣,或在阳光下铺着的兽皮上摇着小磨享乐。在庄严的祈祷仪式上,他们用深色的酒和烧肉来祭奠,高声祈祷他们心中所渴望的,但同时也知道,神在谛听着他们,将施予或拒绝。这一切不只是历史,而且是最好的历史。在文化研究者的眼中,使新人感到如此惊讶的自然和超自然的荒谬结合,是早期宗教思想状态的证据。神祗们在宙斯——乌云的召集者的宫殿里举行会议,以便决定如何处理他们平地下方的信徒们正在厮杀的军队。神祗们参加到了战士们拼死的斗争中。波塞冬从埃涅阿斯的盾牌上拔出了青铜尖的枪,举起这位特洛伊的英雄,并把他无害地带到战士们头顶上空;连女神们也都互相争吵,像那些粗鲁的死去的莽汉们一样。例如,赫拉从阿耳忒弥斯那里夺取了弓和箭筒,并带着轻蔑的微笑用它们射击她的脸,直到她流着泪避开,把她的弓留在后面为止。如果认为这全都是纯粹的虚构,或是最初听到史诗这一奇异章节的人所进行的诗的修饰,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些人还处在上一章所记叙的过渡的宗教状态中,当时,精灵是使原始的祖先成为把自然及其现象的存在人格化的原因,而这些精灵已经开始丧失其鲜明性,但仍然继续被认为是支配自然并干预人们生活的神。我们如将这类思想状态和现代的论断相对照,就能帮助我们认清在整个历史中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人类思维从神话气质向历史气质的过渡。这种变化并非一下子发生,而是在许多世纪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格罗特(Grote)的《希腊历史》中,较之地叙述哲学世纪的那一章来,未必能找到较有教益的章节。在哲学世纪,希腊人困惑而苦恼地觉察出,作为他们的《圣经》的荷马史诗,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上人们跟神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变化可能实际发生吗?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所谓古代历史中的许多现象,也应当以同样的观点来研究。采用历史考证,也就是采用判断,其目的不是为了不相信所报道的,而是为了相信它。它的目的不是从作者那里寻找错误,而是为了查明他所说的哪一部分能够确实为历史所承认。因此,现代的读者,比起李维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来,有了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较为全面的意见。我们比他们看得更清楚些。说由一个叫罗米拉斯(Romulus)的人转成了罗马的名称,这似乎不太可信;不如说罗米拉斯的名字是为了解释这座城为何叫罗马而虚构出来的。要知道,关于喂养了罗米拉斯和雷马(Remu)的牝狼的著名故事,当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希罗多德作为塞鲁士降生史传播的那个故事的异文时,它对新时代就丧失了任何意义。但是,在这里也能看到间接的历史标记,即使它的事件是最不可靠的。尽管世界上或许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存在过像罗米拉斯这样的人,关于他用自己的青铜犁划过城墙地点轮廓的传奇,也是对于古代着手建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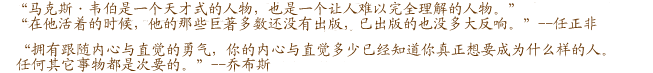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