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四章 精灵世界
| 精灵附体的形式,而这个附体者属于他并到处跟随着他。这种精灵可能是在梦中见到的死去的父亲的灵魂,如粗野的塔斯马尼亚人( Tasmanians)就是这样想;或者是那种像在北美战士们身上的守护精灵,战士在梦中没有看见守护精灵时就斋戒;或者也许就像古代罗马人的守护神——同他一起降生的精灵,是他一生的同伴和保护者。奥古斯都(Augustus)的守护神是一个神,它需要人祈祷和送祭品;但是我们新时代的人却如此落后于古人的思想,继续采用他们的词汇,继续有兴味地以我们在谈到汉德尔(Handel)或特纳(Turner)的天才时所理解的那种已经改变了的意义来看他们的词汇。在我们的思想中,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天空和海洋,山岳和森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学会了观察引力和热量、生长和分解的物理规律的作用,并且只要作一些努力,我们的想象就能转移到那遥远的时代,那时人们在无数精灵中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同时,这种信仰是直接从灵魂论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人们看待这些精灵,就像看待支配自然的灵魂那样;而这种灵魂支配自然,又像人的灵魂支配人的肉体那样。这些精灵从火山中把火抛出;它们在刮台风时折断林中树木;它们使小划于辗转于漩涡之中;它们栽种树木并使之生长。低级种族谈到这类自然的精灵,而且对待它们完全像对待特殊的个人一样。这就证明,它们是被按照人类灵魂的型式创造的。新时代的旅行者们看到,船行在危险地段时,向河中撒一撮烟草,向河中精灵祷告,祈请允许渡过。非洲的樵夫,对大树砍第一斧的时候,倍加小心,并且在地上滴一点椰子油,让被激怒的树精灵从树中出来时停下来舔,这时樵夫就可以逃脱性命。希腊人曾这样想象:令人神往的溪谷、河流和茂盛草原的山林水泽女神们,来到奥林波斯诸神(Olympian gods)的会上,坐到明亮的座位上;或者是林木女神们同绿荫如盖的松树和橡树一起生长,当樵夫的斧头砍入树干的时候,她们痛得大声号哭。——这时,希腊人应当是有这样的智力状况,即早就有这些关于自然精灵的观念。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辞典中保留了一个有趣的词“woodmare”来表示“回声”(wuau-maer——森林的女神)。这是关于下面这个时代的遗迹:当时英国人相信——也像野蛮人那样信仰,回声是精灵回答的声音;表示精灵或魔鬼的词mare,也出现在nightmare——“梦魇”这个词里。梦魇就是梦中见到的使人出不来气的魔鬼。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它是同样确实存在的;它对于现在的澳大利亚土著来说,仍然如此。被自然科学所消灭的古代的自然精灵,仍然在诗歌和民间传说中找到了自己的藏身所。洛勒莱仅仅是那种使泅水者沉入漩涡的水怪的更新的异文;古代圣典中改邪归正的水的精灵,都是采用了基督圣徒的名字;小精灵和林仙仅仅是对古代森林的精灵的模糊回忆。赫肯黎的《地文学》的读者们,在魔法故事中知道那些自然的精灵原来是史前人所想象的自然力的人格形态之后,将会感到惊讶。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除了一群灵魂、精灵和自然神灵以外,所有部族的宗教还都承认有高等精灵或神。在盛行祖先崇拜的地方,这种神之子就可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或战士或著名个人的灵魂。例如,蒙古人把伟大的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崇拜为善神。中国人声称,木匠和建筑者把很久很久之前生活在山东省的著名技术家鲁班尊为自己的保护神,而关帝为战争之神,他是汉朝的杰出战将。祖先们的神性观念如此发达,甚至获得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例如,祖鲁人当从一个祖先精灵上升时,他们说到温库隆库鲁( Unkulunkulu),即陈年老者,就像说到世界的创造者一样。再如巴西的部族说,塔莫伊(Tamoi)爷爷是第一个人,他生活在人间,教会了人们耕种田地,然后就升天了,在天上接收人们死后的灵魂。在自然精灵中,野蛮人也明确提出支配宇宙的大神。非洲黑人的最高的神是天,它降雨并让草木生长;在早晨醒来时,人们向它致谢,因为它启开门户,太阳就出来了。可见他们也像雅利安人的祖先一样,处在同样思维发展阶段上。雅利安祖先的大神就是在《吠陀》圣歌中所赞颂的戴乌(Dyu),它同时是降雨和打雷的天的化身,也是赋予它以灵性的天神。这个神即使有自己的名字,它仍然是希腊的宙斯和拉丁的朱庇特天神。两种宗教保留着它那属于野蛮人神学的天和天神的双重意义。这种野蛮人神学也允许天空或天体众神生活,或者说这种神学也用按照人的灵魂创造的在那里生活的神来解释这种生活。如果我们想象神是天体的灵魂,那么最好是能够了解,天神意味着什么。在所有野蛮人的宗教残余中,很难找到某种比下面这些至今还承认活生生的天等于神的语句更有表现力的句子。例如:“老天宽恕我吧!”“他遭到了老天的报应。”下雨和打雷大都被认为是天神的事,例如,宙斯投下了毁灭之箭并撤下了暴雨。但有些民族有专门的雨神,如奥里萨的孔德人(Khonds),他们向皮祖·宾努( Pidzu Pennu)祈祷,请他将水通过筛子灌浇他们的田地。另一些民族有民族的雷神,如约鲁巴人,他们说,他们那带有闪电和响雷的尚高(Shango),把他那毁灭性的斧头抛到了地上,他们从地中间把这些斧头挖掘了出来。我们英国人还记得在我们的词汇 Thursdar(星期四)中的 Thunder或Thor(雷神),Thursday就是Dies Jovis的翻译。大地.万物之母,在野蛮人神学中占有她的地位。例如,奥基伯威族中虔信宗教的印第安人,在挖他们的药草时,总不忘给大地曾祖母留下带来的某种礼物。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的幻想也不可能比下列的观念鲜明,即无父和地母到处都是万物的双亲;任何形象也不可能比中国的婚礼那样更自然地代表它们:在中国的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向天地跪拜。在古典宗教中,他神是十分鲜明的,得墨忒尔,地母,大概是我们对她崇拜的最后痕迹,可能就是在田地里留下最后一捆未割的庄稼,或者把最后割下的一捆庄稼隆重地运到收获主人的家中。在几内亚海岸的黑人中间,可以发现新时期关于海神的最明显的观念。在这里,土著皇帝为了恳求海神不兴风作浪,将稻米、布匹、瓶装的甜酒甚至奴隶作为祭品扔进海里。某位希腊或罗马的统帅在把自巴托身于险恶的海浪之前,同样带上了公牛作为奉献给波塞冬或尼普顿的祭品。对于那些能够像看待有灵性的、有理智的人那样来看待天、地和海洋的人来说,太阳具有最明显的神人的个性,因为它给予世界以光明和生命,它升起并横过天空,在夜晚又陷入地下世界,后又从那里升起。在一个萨莫耶德女人每日祷告的故事中,有原始的纯朴记述。当太阳出来时,她向它俯首行礼,说:“当你,上帝啊,起身时,我也起床”,到傍晚,“当你,上帝啊,躺下时,我也就休息”。太阳之神出现在最遥远的历史时期,例如在绛红色埃及箱子的画上,就可以看到乘船沿着宇宙的上下部分旅行的拉(Ra)——太阳神。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婆罗门教徒,这些现代的老年人,一只脚站着,两手伸向前方,面对着东方:他们这是在对太阳礼拜。他们每天重复地向太阳祈祷:“我们思考着非凡的太阳神的希望之光;太阳神将唤醒我们的思想!”月亮神或月亮女神标志着粗野的林中部族的祝典,他们在满月的光照下舞蹈。月亮每每高于太阳,例如,在古代的巴比伦就是这样,这可能是由于天文学的原因。但是,更为普遍的是太阳神处,首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较为自然的;太阳和月亮通常被认为是一对——兄妹或夫妻。不难了解,在叙利亚著名的庙堂里,为何没有类似所有其他神像那样的太阳和月亮神像,因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所有古代的自然神中,它们还单独地受到了我们个人的崇拜。在德国和法国,至今还可以看到,农民在升起的太阳面前脱掉帽子;而在英国,对新月则鞠躬致敬或屈膝行礼;而“翻转银币”的有趣习俗,显然是英国拿金属给月亮作祭品的遗留。火,虽然它未必能达到一等神的高位,但是,它被看作是一个人物,并且人们因为它既带给人恶、又带给人善而加以崇拜,还把它作为上帝的仆人来崇拜它。在雅利安民族中,《吠陀经》的第一个词就是阿格尼(Agni), 即火神(拉丁文 ignis)——供献牺牲时的神祭司的名字。古代波斯宗教的代表者袄教徒是典型的拜火教徒,他们的最神圣的地方是燃烧之源巴库(Baku)旁的神殿。在古代的希腊人中,赫斯提亚——圣炉受到了油食和甜酒的祭扫,而她的名字和对她的祭奠也传到了罗马,进入了威斯塔庙,在她的殿堂内燃着永不熄灭的火。风神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和在南太平洋的岛民中,也像在希腊人中一样闻名。它们自希腊人的宗教一直传到了现在,每一个农夫的孩子,现在都听说过严酷的玻瑞阿斯和温和的仄费洛斯。为了结束这个名单,我们将说,与溪流的小精灵相比,江河是如此高级的灵物,它们往往有自己的庙宇和自己的祭司,例如,斯卡曼德罗斯(Skamandros)和斯佩乔斯(Spechieos),人们以它起誓,因为它能够使违反誓约者在它的深渊中浮起和沉没。对于印度人来说,至今最可怕的誓言就是以某一神河——最大的恒河发的誓言。 这类神的名单,有助于多方面地阐明多神教,而这种多神教在地球的各个部分都有。这些神即天、地、海洋、日和月以及其他伟大的自然力的巨大灵魂,同时每一神物都有其神的个性,有其在世上的自觉的目的和工作。但是,要阐明多神教的各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论是在各部族中,还是在许多神的属性中,都发生了混合。在许多庙宇里所供奉的神,倾向于分成若干个别的神;人们在遗忘其原始意义之后,继续崇拜各种名义之下的个别的神。在彼此融合的各民族之中,由于联合或征服,宗教也互相混合了,而各种不同的神也丧失了其固有的个性。古典的辞典也充满了这类例子。响雷的天和多雨的天,雷神和雨神(Jupiter Tonans和Jupiter Pluvius),是后来作为两个单独的神物而被崇敬的。古罗马人的尼普顿和希腊人的波塞冬,因为它们两个都是海神,就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很有兴味的神的混合体。在商业神墨丘利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古代的神,希腊的赫耳墨斯,是伴随死人到冥国去的神之公使,是盗贼和商人之神,文字和科学之神,它也具有由若干更早的神所组成的痕迹,其中有古埃及的文字神托特(Thoth),它生有神鹤之首。这能够提供关于发生在宗教中的那种混乱的概念,崇拜者们很快就不再去想该神的原始意义和使命,而只是把它作为该庙中所塑造的这一个神来认识。在现代,很难确定如此众多的古代神纸的来源,这是不应当感到惊奇的;但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与其说它们最初是神化的祖先,或是太阳,或是天,或是江河,毋宁说它们之中还有如此多的神,在上述这点上竟表现得如此之鲜明。野蛮人的宗教之神同样清楚地表明,在野蛮人的神学者们的头脑中有一种思想在活动,而这种思想在高级文明阶段上注定地获得了巨大的作用。在观察犹如善的精灵和恶的精灵相互大战之原野的世界时,有一些宗教提出,这是两支彼此战斗的军队,在它们的上面有高级的善神和恶神,而在所有它们之上还有最高的善神和恶神。这种二元论的体系——正如人们所称呼它的,是在古代波斯的宗教中,在善和恶的精灵阿明拉·玛兹达和安格拉·曼纽之最高统治下,光明和黑暗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形成的。在较为文明的民族的宗教中十分著名的那种神的等级制度,在野蛮人的宗教里也同样有粗略形式的表现。就像信徒们本身有普通人和他们上面的领袖,以及拥有执行其命令的高级和低级官员的伟大统治者或皇帝那样,信仰者们也在自己的神中间建立了神的低级和高级序列制度,设置了最高的神。这种最高位的神应当属于哪一种神,并非处处一致。正如已经指出过的,把死去的人的灵魂认作是自己的神的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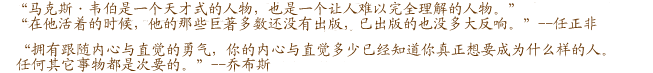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四章 精灵世界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