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
在从前还没有法学家和法典的那个时代,那些庄严的法令和权利借助如画一般的仪式,使它对所有的人都变得鲜明,这些仪式能够在没有知识的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古代仪礼在现在还保留着,并且如从前一样鲜明地表现出它的意义。例如,当双方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时候,他们就举行一种合血的仪式,为的是变成为血统亲戚。在现时,旅行家们常常跟各种野蛮部族结成这种血统的亲戚关系。有个关于举行这种仪式的东非人的故事这样叙述着:两个人一起坐在兽皮上,意思是他们共有“一张皮”,然后一人在另一人的胸上割开一些小口,收起混合的血,把它擦入另一人的伤口中。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希罗多德所记述的,在古代的吕底亚人和斯基泰人中所采用的,在古代诺曼人的传说及古代爱尔兰的传说中也同样提到过的那种契约形式。要较为明确地说出古代道德学说的最重要的原则,那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学说,人彼此一般不应当是不相关的,而只能是自己的亲戚,因此,不很干的人,为了获得抚爱的权利和真诚的态度,就应当变成血缘亲属。由于思维体系相同,甚至粗野部落也认为吃、喝跟缔结友爱关系的活动是相联系的,因为在某种氏族内,客人可以成为家人之一,而且在道义方面,对待他们应当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人们到处都对一起吃饭的事实所赋予的那种重要性。在亿万印度居民中,在现时,社会的结构本身回旋在等级制度之中,有的人能够同他一起吃饭,有的人就不能同他一起吃饭。在结婚仪式中,远东非常著名的结婚仪式之一是:一对男女共吃一盘饭之后就成了夫妻。从印度的结婚典礼中可以看到,仪式怎样通过比较恰当的隐喻而获得意义。在那个典礼上,把新郎和新娘的衣服前襟结在一起作为结婚的标志,新娘把一只脚踩在石头上,用来表明她将像石头一样坚贞。据说,在上世纪的英国流浪人中有这样一种习俗:男子和女子的手在死动物身上结合起来,以这种方式来预示,他们将结合在一起,至死也不分离。在罗马法庭上的几个场面,是属于欧洲法律中著名的戏剧性的仪式。在那个法庭上,奴隶主提出他对奴隶的要求,于是上前用表示枪的木棍来触动这个奴隶。或者像在古代日耳曼人的习俗中,一块土地的转让是用这样的仪式来表示:从森林小草原中取一块带草皮的土,上面再插上绿枝;土地的原所有者亲手把这块上交到新所有者的手中。或者如在封建时代的法律活动中,一位诸侯把自己的双手放在封建君主的两手之间,这样也就“把自己交到了他的手中”,于是就成了他的下属。 在古代的法权中存在有另外~些仪式,它们比上述这类手势语还要实际些。野蛮人的法律在早期就已经开始祈求魔法力和神力的帮助来解决困难的任务:揭露罪犯,迫使见证人说出真情,必须实现许诺。这就导致了广泛流行的神裁判制(法律的考验)和誓言。有一些神裁判法,实际上是用来揭露真象,因为它们影响罪犯的良心。例如,关于一撮米的事,在印度,被认为可疑之家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把这一撮米放入口中,而小偷神经紧张,这就妨碍他把米吞下。在英国,同样用一块考验性的神圣面包或干酪(corsnaed)来做;甚至现在,农民们也还没有忘记这套旧公式:“假如我撒谎,我就让这块食物噎住!”留在人民记忆中的不多的神裁判法的另一种,我们可以在下述情况中看到;在某个远方的农场主家里,强迫所有被认为有偷盗行为的人都握住《圣经》;《圣经》被系在一把钥匙上,而这《圣经》在小偷的手里难免抖动。古典社会用悬挂在张开的剪子尖上的筛子进行的占卜,也用这种形式保待了下来。神裁判法已经落伍于时代,现时已为大多数文明民族的法律所驱逐。在现代,若要见识受法律许可的烧红的铁考验,那就必须到那些像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去。在英国,这种考验只有在那些天才实地运用,那就是当讲述关于走过烧红的犁头的艾玛(Emma)女王的传奇时候。现在,这种古代的观念在厅堂里还由变戏法者体现着。就在不远的年代里,大家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英国的农民们把一位被怀疑为巫神的老妇人沉入水中,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重演古代的用水考验;而在这种考验中,神圣的自然力拒绝不信神者而接受公正者,所以有罪者能游泳,而无罪者则沉没。这种审判仪式构成了印度的摩奴(Manu)法典的一部分;在英国的法律学中,直到十三世纪初之前,这种审判仪式都是考验被控告犯有杀人或抢劫罪的人的合法手段。如果受到神的裁判的人有罪,那么,通过神的裁判,他就会招致某种灾难。这种神裁判法本质上跟誓言相近似。但是,誓言通常是招致上天的未来惩罚,这惩罚是在现世或在来世。例如,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法庭上,可以看到奥斯加克人宣誓的有趣场面:当时,把一个熊头带到法庭上来,为的是如果见证人做了虚假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奥斯加克人就去咬这熊头,以此为誓召唤熊咬死那见证人。在我国,法庭誓言在其外部方式上带有远古的痕迹。在苏格兰,见证人把一只手举向天空;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用这个姿势,请至高无上的神降到见证人身上,并请求神对违反誓言者的头进行报复。在英国,吻《圣经》(“新旧约全书”)出自触摸圣物的习俗,类似古代罗马人摸祭坛或宫廷承宣官摸圣徒遗体箱。“上帝帮助我”(So help me Got)的形式,是从古代条顿-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法学中继承下来的,按照这种法学,古代的诺曼人摸着祭坛上染血的环发誓说:“只要弗雷(Frsy)和尼奥尔特(Niordh)和全能的神(也就是雷神)帮助我。”一个和最末一个是古代的英国神,我们(英国人)把他们的名字保留在 Friday(星期五)和 Thursday(星期四)中。 现在我们转到本书的最后一个课题——统治史。无论文明民族的政治机构如何复杂,只要我们在蒙昧生活和野蛮生活中找到已有的简单形式,对它的研究就变得较为容易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家庭的自治是社会的基础。它的权力的代表者就是家长。例如,在巴西森林中的低级野蛮部族中,父亲可以随意处置他的妻子和孩子,甚至把他们卖为奴隶,而邻近的人既没有权力、也不愿干涉他的处理。在现时,文明民族都承认,出生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生活的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即使是这一点,在低级种族中都未必被承认。在澳大利亚人和许多其他蒙昧部族十分艰难和困穷的生活境况下,人们由于贫苦常常把新生的婴儿消灭掉,因为在双亲身分已经有了他们所能喂养的几张嘴。在这类部族中,由于生活困难而杀婴,较之由于残酷无情而杀婴进行得更干脆。这一点常常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双亲到火里或水中去救他们几周前还在犹豫是应该让他活还是让他死的那个孩子。甚至在那些为生存的斗争不再如此严酷的地方,悲惨的杀婴习俗仍然还十分普遍。没有任何能较为清楚地证明,欧洲民族所经过的野蛮状态,像在古代罗马人和我们条顿人的祖先中所见到的那种法律一样,并且按照这种法律,要不要养育或遗弃新生婴儿全由家庭的父亲决定。婴儿既然成为家庭的成员,他的生命就有了点保障;当年轻的野蛮人成长起来,成为战士,后来又成为新的家长,一般地就成了自由人。但是,最古的罗马法律允许家长进行严厉的统治,其严厉性是我们新时代人的思想所难以理解的,因为父亲可以对自己成年的儿子进行体罚或者把他们处死,可以强迫他们结婚或跟妻子分离,甚至把他们卖掉。随着文明的进步,在罗马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儿子逐渐获得了本人的权利和财产权。当把古代社会的生活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相比较的时候,基督教信仰就变得明显了:关心的不是家庭的权力,而是个人的灵魂,渴望个人的自由。在现代生活中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家庭专制主义的最好的特点仍然有作用,孩子们从属于双亲的权力之下,为了完成自己未来的义务而继续在受教育,法律在赋予孩子与双亲相对的个人权利方面,极为慎重,以便不削弱那种把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基础。但是,因为家庭已经不再是像它从前那样的在自己内部的独立王国,于是个人就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粗野的社会中,在发生某种罪行的情况下,受害的家庭就向犯罪者的家庭复仇。关于权利的新观念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让无罪者代替有罪者受处罚。但是在低级野蛮人的生活中,实际上这是维持秩序的最好方法,并且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种习俗下的人来说,这是正确而合理的。例如,在澳大利亚人中有这种习俗,在这里,当某一家庭成员杀了人,其余的成员自然而然地承认他们也有罪。这种观念完全不限于一些蒙昧部落,研究家在像希腊人和罗马人这样一些古代民族的法律中,也熟识这种观念。在这里,只把欧洲法律中出色的地方引出来也就够了,这样的地方同时证明,古代的原则是什么,并如何将这种原则加以改造,把高级的法权观念加入到法律中去。“父亲们不应因孩子们而被处死,而孩子们也不应因父亲们而被处死;每个人都应当因自己个人的罪而被处死。”(“第二诫律”二十四,16) 在蒙昧地区的旅行家,在哪里都会遇到一些顺着荒原一起游牧的家族,或者都会见到一片热带森林中小河旁的茅屋——只要他十分注意地观察,他到处都会发现某些统治的萌芽,因为到处都有某种涉及整个小公社的事,如选择居住的地点,或调解跟沿河远一点的邻近部族因捕鱼而发生的争吵。即使是在格陵兰人——或许这是全世界管理程度较低的民族——中也可以看到,如果一些家族整个冬季都一起生活,人们就在雪屋的北端给某一位善于预测天气的老渔夫一个地方,委托他照看其余的居民,并关照他们,让他们修理雪墙,从家中出去要一同回来,以便不浪费热量。同样,当他们结队出去狩猎时,推选某位有经验的向导作为部队的领导者。在蒙昧部族中常常见到这类领导者或领袖,他们由选出来的那些地位最重要或最灵敏的人来担任。但是,这类人对于家庭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权力,是通过说服和借助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当然,这类领导者的家庭同样也具有作用,或者,如果还没有,那么,他就要努力使它具有这种作用,因此,在他的职位上就表现出了一种变成世袭的意向。在母系氏族中,领袖自己的儿子可能没有继承权;在以母系氏族为基础组成的部族中,通常是前任者的幼弟或母、方的外甥被选为新领袖。在存在跟我们非常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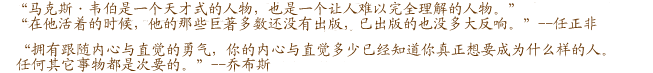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