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
| 他是从最早阶段按迹探求法律学的历史的话,他实在应该把这两个原则清楚地记住。他将在近亲复仇的原始法律中看到,社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利用了把人跟低等动物区分开的近亲复仇的天性;同时由于认为整个家族对它的每一成员的行动都负有责任,社会就利用家族对每个人的影响力,作为保持人们之间和平的手段。无论是谁,看到近亲复仇的影响时就不能否定它的实际合理性,也不能否认它在那种还没有专门的法官和刽子手的阶段上,对于制止人的暴行的益处。实际上,所有蒙昧人和野蛮人中的近亲复仇者,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暴烈疯狂之中,由于流血的事业而履行了自己的一份使自己的民族免于灭亡的义务。不幸的是,那些把他的复仇指向无辜者的愚昧和谬误,常常损害复仇的效用。那些属于许多蒙昧部族之中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如果他不杀害,任何人也都能死亡,因此,他们就用下面的信念来解释我们所说的自然死亡:某个敌人借助魔法用看不见的武器伤了死者,或者派病魔吃掉他的内脏,这样把死者杀害了。因此,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就借助占卜来着手侦察使他死亡的凶恶巫师。当他们说到了谁的时候,就把谁当做了暗藏的敌人,复仇者就去寻找他并把他杀死。当然,这时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方的复仇:于是就发生了祖传的敌对性。这是部族之间怨恨、仇视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蒙昧人处在经常的恐惧和不安的状态之中。当转到研究高级文明水平的时候,我们在古代文化水平高的民族中仍然遇到了近亲复仇权,但是它已经被文明逐渐改变了形态;在现代,文明已经把它彻底灭绝了。例如,以色列人的法律仍然允许近亲复仇,同时建筑城市,建立避难所,对于那种在道义上无罪的杀人者,不应当看作是包藏祸心的人。在那些已经积聚了财富的民族中间,特别是在人们到了用金钱来评价人的那个阶段的民族中,古代那种关于以血来复仇的疯狂呼声,就转变为要求酬金。在阿拉伯至今还能够看到与这种发展相比邻的较早和最晚的阶段。虽然沙漠上的游牧部族贝都英人,一代代地在继续进行野蛮的流血斗争;而城市居民们则认识到,杀人者们在每条大街的角落里等候每个人,在生活中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他们花血费并停止斗争。这种事态在下述这一方面来说,是可资借鉴的。在我们的早期祖先中,事态是同样的,当时按照条顿人的法律,人仍然有为那种给他或地的亲属所造成的伤害复仇的义务——只要他还没有进行金钱交易。用于这类和平交易的钱盎格鲁撒克逊语为wer-gild,意思是“赎人钱”——赎一个自由人二百先令,赎低等人较少,赎一个威尔士人(Welsh)比赎一个英国人少。其次,在那个复仇的常规仍然是要求以命抵命的地方,受小辱也同样要以罗马的lex talionis的方式,或“同等法”的方式来报复;我们英文的retaliation即“报复”,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一点由犹太人的法律:“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皮带抽打还打”,明确地固定下来了。在阿比西尼亚,报复还仍然是法律。还在不久以前,那里有一位母亲追究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偶然从果树上掉下来把她的小儿子砸死了。法官们判决她有权派她的另一个儿子到树顶上去,让他从那里掉到那个并非有意砸死她的小儿子的孩子身上;但是,她不愿意运用这样的权利。当然,报复开始逐渐温和而变成了罚金,例如,古代的英国法律保障着,如果谁切下了另一个人的手或脚,那么这个肇事人就必须赔偿损失者整个人的半价;一个大拇指赔偿一只手的半价,等等,直到一个小指赔偿五先令,一个小指的指甲赔偿四便士。在现代,法权已经过渡到高级阶段,国家肩负着处罚一切由它的公民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职责。当读到某种关于科西嘉人的族间血仇(Vendetta)的流血故事的时候,我们未必会想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继续存在于荒凉的山岛上的古代法权的遗留。其实,我们的刑法法规就是从这类私人复仇中发展而来,这一点,对于注意过去遗迹的人来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当听到类似“法律复仇”的说法,或对那意味着由于它而个人有权追究欺凌者的诉讼法的东西进行思考的时候,蒙难者好像在很久以前的时代中一样,仍然记得复仇或取得赔偿。在现代,实际上国家本身因为社会司法的缘故而力图惩处罪犯。复血仇者在某个时期曾经是社会安全的守卫者,现在如果他自行处理,那么自己就要成为罪犯而受处罚。而道德学者,注意到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确定了常规:复仇是犯罪。
法律虽然已经如此有益地取代了个人复仇,但是它还没有使较大规模的争吵——国家之间的争吵,完全受自己节制。个人复仇跟社会战争之间的联系,在粗野部落之间,例如,在巴西森林居民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部族内部出现杀害行为的时候,那么复仇当然就是与杀害行为有关的两个家族的事;但是,如果杀人者是属于另一个氏族,那么,他的事就变成了反对整个社会的罪行。受欺侮的社团就召开会议,并做出了——只要敢做——大部分赞成战争的决定。然后派出军队,在最前面首先投入战斗的是死者的亲属,他们的身体都涂上黑色,以显示他们在履行杀人的天职。邻近部族间开始战争的一般途径,是争吵或侵犯疆界,然后是某一方的人被杀死了,为其死者的复仇就发展成为流血的斗争,而部族战争总是准备一代又一代地爆发。这种野蛮的事态也曾长期存在于欧洲历史上。按照古代的日耳曼法,任何一个身体、荣誉或财产受侵犯的自由人,只要他不同意法律协定,换句话说,他拥有个人战争权利;那么,他可以求助于自己的亲属为自己复仇。国王艾德蒙德(Edmund)颁布了限制这种“非法战争”的法律,这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这类战争不是一下子能终止的,特别是在诺森伯兰郡。我们知道,在蒙昧的苏格兰高原地区的氏族中间,这类战争即使现在仍在继续。在普通的自由人停止了跟邻人的斗争之后很久,某些贵族仍然保持自己的古代法权。甚至还在爱德华四世(Edward IV)时代,伯克利(Berkeley)勋爵及其信徒们,在格洛斯特郡的尼布莱·格伦(Nibley Green)跟莱尔(Lisle)勋爵发生了战斗。莱尔勋爵被打死了,最后,伯克利勋爵用金钱交易跟他的寡妇了结了这件事。弗利曼(Freeman)在其《比较政治》中,回忆到十五世纪历史中的这一使人感兴趣的事件时,认为它是最后一个英国个人战争或支付赎人钱的例子。禁止个人战争的英国法律是民族进步中最伟大的步伐之一。现在,国家采用在法院中进行审判的方法,以代替个人复仇和个人战争的野蛮手段。但是各个国家继续用战争来解决它们的争吵,而这种战争跟过去氏族之间的流血斗争相比,也是同样的,只不过是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罢了。 和刑法法规相类似,关于私有财产的民事法规可以溯源于原始概念。通过研究早存在于非文明世界和存在于现代的关于财产的这类法规,可以获得关于早期财产关系的正确观念。在低级种族中,我们的法学家在不动产和动产之间所作的区别,表现得极为明显。土地为所有人使用,但是任何人也不能把它作为专有财产。最简单的土地法是跟关于狩猎权的法规合在一起的;这种土地法可以在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部族中看到。例如,在巴西,每一个部族都具有以岩石、树木、天然水沟或者甚至人工界标为标志的疆界。在追击禽兽时破坏了疆界,就被看作是如此严重的事件,以致犯罪者可能被就地杀死。在这类社会状况下,在这无论是怎样的世界的一部分里,每一个人都有权在自己本部族的疆界之内狩猎。禽兽只有被打死之后才能成为个人的私产。因此,这里有关于那种属于氏族或部族的土地公有权的明确的法律概念。也有关于家庭所有权的鲜明概念:茅屋属于家庭或家庭群,属于它的建筑者;当这一群体把茅屋附近的一块土地圈起来并加以耕种时,这块地也就不再是社会财产而变成家庭的财产,最低限度,家庭暂时借用着它。茅屋中的器具如磨制的石块和陶罐,也属于每一个家庭。同时也出现了个人财产,虽然还是在那种由父亲或家长体现出的族权之下表现出来的。个人财产主要是由下列的东西组成的:每个人身上带的或直属于自己的东西——武器、装饰品、上下身的微薄衣服;家庭的成员有权制作的生活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死后大部分要带到阴曹地府去。 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野蛮人已经熟悉了下列的概念:土地公共所有,家庭土地自由占有(freehold),家庭和个人的动产——这些概念组成了古代法权的整个体系。但是,这些概念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农村公社在使亚洲和欧洲住满居民方面起过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在现代的英国还有它的痕迹;而在这种农村公社里,不仅狩猎的地方和草原是公共所有,家庭甚至连所耕种田地的所有权都没有。这些田地是共同耕耘,有时或在各种经济作物之间再分成若干区段,因此分拨出的家庭所有只限于房屋和菜园。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军事民族的产生导致土地所有制的较早方式发生变革。在被侵占的地方,战败者的土地被分配给王公或他的部队的长官或普通战士;而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把取得这种土地作为应尽的义务。这类最大最好的著名例子,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英国,到威廉征服时,原先还是国家公共所有制的人民土地,已经开始过渡到国王手中,所以国王对它能独自酌定如何分配。或者,在军事国家中,国王能够成为一切土地的所有者,同时允许他的臣民占有各部分,每年缴纳贡品或税捐:这就是十分著名的古代埃及和现代印度的制度。在罗马历史上,我们发现,国家或家庭占有大量的土地,把土地一部分作为一种形式分配给佃农,而征收其一部分产品。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地租的产生,而这地租是原始法权中还不明确的一种关系。同时,正如在土地占有方面所发生的这些变动一样,动产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变为耕种土地的奴隶的战俘,成了家庭财产的一部分;而收人生活导致牲畜不只是用来做食物,而且也用来耕田。贵重物品的生产,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和钱币的使用,给这增加了其他的财产形式。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使用财产的新手段,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多么巨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取消了家庭手中的财产,而允许由个人所有者来掌握和支配;而这是如此适合于我们这个具有积极的工业进取精神的时代的制度。甚至土地都可以由个人买卖,虽然法律为田地和房屋的转让,较之钻石项链或成百箱茶叶的转让制定了另外一种程序,制定了繁杂的手续,高昂的价格;与此同时还仍然保留着古代制度的痕迹。在古代的制度下,土地由一个所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假如这种转让是可以的——一般是很难进行而且要由许多人同意。尽管有这一切变化,古代的家庭所有制仍然继续保持着:指出这一点是极为有益的。根据一个人死后他的财产如何处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从前的两种最普通的方法,那就是:或者是财产不分,一家人仍在一起生活;或者是财产由孩子们或儿子们分掉。当长于是家庭的宗法之首的时候,他为了维护这个体统,能够以“长子继承权”的名义获得特殊的或加倍的一份。这是雅利安族和闪米特族所共同熟知的古代习俗,因为它既出现在印度的古手抄本法律中,又出现在《申命记》中。在法国,这种古代分配财产的原则至今仍然受到法律的支持,家庭的成员按其权利而获得其应得的一份财产。在英国,遗嘱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在理论上,一个人可以随意拒绝把全部财产给谁,但是在实践上,受到道德感和舆论的内在约束。这种道德感和舆论好像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类剥夺孩子的资产而让一个旁不相干的人或者某一座医院发财致富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如果一个英国人死了,没有留下遗嘱,法律承认他的家庭的权利,把他的动产公平地分配给他的每个家庭成员。而土地财产或不动产则按其他方式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转归于长子。为什么法律如此承认所有其余的家庭成员有权分钱而无权分土地,这是极为有趣的历史问题。梅因(Maine)的《古代法》的读者知道,千年左右之前,在欧洲,形成占有地的土地开始归属于长于完全不是为了使他致富,而是为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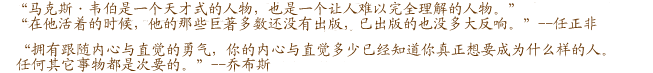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