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
| 关于蒙昧人生活的事实,阻碍着我们重温上世纪哲学家们的梦想。那些哲学家提出,“高尚的蒙昧人”作为德行的真正范例,很值得文明民族效仿。然而事实始终是十分富有教益的,因为它证明,美德和幸福的法规在那些用磨利的石头做斧头、用木棒互相磨擦取火的部族中,原来是采取简单的形式来实行的。他们的最好生活异常清晰地证明着伟大的伦理原则,即道德和幸福是携手并肩而行的,事实上,道德是获得幸福的方法。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不应当设想,在任何文明状态下,人的行为都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善和恶的道德感。即使是在蒙昧人中,社会的管制力也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比起在我们中间来是萌芽的形式罢了。舆论已是伟大的力量,应当特别注意它借以发生作用的手段。各个个人极易关心自己的利益和自己亲近朋友的幸福,但是当某些思想同时活动,当具有大利己思想的舆论保卫共同的幸福,激励个人把他的私人愿望抛在一边,并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有财产甚至生命的时候,则这些私人的动机就消失了。全部族作为一个整体,它能够蔑视那些卑劣者和怯懦者,或者对那些用全部幸福和自己生命来冒险以争取荣誉的勇敢成员给以奖励。旅行家们指出,妇女无论怎样受压迫,她们也能了解自己在这方面的影响。许多在敌人面前内心动摇的战士,想到他们没有带伤而带着耻辱回到自己的村中时姑娘们的嘲笑,于是他们就坚决挺住而不临阵脱逃。这种舆论方面的压力迫使人们按照习惯来行动,而这种习惯提供了在生活的大多数情况下何者该做、何者不该做的规则。蒙昧地区的研究者们没有发现警察机构,而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是习惯于有这种机构的。他们有时极大胆地断定,蒙昧人的生活无拘无束,每个人都随意而为。我们已经指出过,这是错误的,因为文明社会中的生活每一步都被习惯的锁链牵制着。十分明显,习惯是由于社会的福利或者是由于被认为是社会的福利而产生的。例如,在蒙昧地区,一般认为热情接待一切到来的人是好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某个时候他自己就可能需要这个人。但是,习惯是明显有益还是无益呢?一度它被断定说,不得不顺应它,即使当它的目的被遗忘的时候。有对蒙昧人被迫切断指节,或者遭受如此长期而严酷的斋戒,以致其中的许多人死亡。但是,作为他们祖先之习惯的那种事实,往往是他们用来解释使自己受难的唯一原因。在澳大利亚的有些地区,习惯禁止青年猎人吃许多种野禽及野兽的最好部分,目的是为老人保留。毫无疑问,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共同的幸福,因为有经验的老人已经不能经受狩猎的劳累,而能够留在家中织网,制作工具,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他们是人民智慧的保存者和受尊敬的部落顾问。没有什么能更清楚地证明,即使是在荒野的这类蒙昧居民之中,社会跟一种单纯的暴力统治相距有多么遥远。由此可见,社会无论怎样古老和粗野,总是具有它们的关于好坏行为的准则。但是,至于谈到什么行为应该认为好,什么行为应当认为坏,研究者应当避免成语所说的以已度人的错误。为了避免根据自己的新观念对处在其他文化阶段上的各民族的习惯做出判决,研究者应当借助想象来唤起自己的认识,以便以各民族所从属的观点,按照从各民族中所获得的结果来看它们的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能说明,关于好和坏、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准则,对于一切时代的一切人并不是一样的。为了用事例来说明这种情况,我们看一看在各种不同的文明道路上,人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老人的。某些低级种族,对老人关怀备至,甚至在老人陷入昏愚之后,对他们仍然几乎是细心照顾,常常是极力服侍他们一直到死。当时由对活祖先的尊敬,转为把他作为祖先的精灵之一来崇拜。但是在有些部族中,儿女们的爱过早地就终止了,如在巴西的蒙昧人中所看到的。他们用棍棒击头来结束自己的病人和老人的生命,甚至把这些人吃掉,是发觉担心这些人是极为重累的事情呢,还是实际上想到——正如他们所说的——这是一种结束既不能以战斗,又不能用宴会,也不能用舞蹈来引起较多快乐生活的好办法。我们能够明显想象出流浪部族中的事态。族群应当为了寻求禽兽而转移,不幸的身体衰弱的人不能支持长征,狩猎的男人和负担沉重的妇女不能够带着他们,他们必须留在后面。许多旅行家都在荒野里看见过这类令人伤心断肠的景象,例如,卡特林(Catlin)当他告别了白发苍苍,几乎完全失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老部族首领庞卡(Puncah)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情景:这位首领颤抖地依偎着几根树枝堆成的黄火,仅用一张水牛皮架在木棍上撑开作为遮障,食物仅有一小碗水和几根半啃光的骨头。当部族出动去寻找新的狩猎地的时候,这位老战士出乎自愿地被抛弃了,这就像在许多年前他自己——按照他的话说——留下了自己父亲的死亡一样。当时他父亲已经变得什么也不中用了。当民族转向了农夫的定居状态,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富裕和居住的舒适的时候,就必须停止为杀害老人或不予帮助地遗弃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了。但是历史证明,这种习俗即使在欧洲也长期地被保持了下来。停止上述辩护,一部分是由于人要结束这长期苦难的意愿,但更多的是因为从较为残酷而粗野的时代所承继下来的那种习俗的体验。住在现在成为德国一部分地区的文德人,保持了令人厌恶的杀害老人和病人的仪式,把他们煮着吃,就像希罗多德所描写的古代马萨格特人所做的那样。在瑞典的教堂里保留着一些特别粗笨的木棒,称作“家族棍”——有些一直保留到现在,在古代,亲属们用它们庄严地击毙年迈的老人和救活无望的病人。在德国的证据中探索从这类古代的野蛮行为向较为温和的习俗的过渡是很有兴味的。在这种温和的习俗下,虚弱的、年老的家庭长辈,把自己的财产分配给孩子们,然后,应当受到他们的尊敬,坐在灶旁的“猫位”上。进步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提高了人类生命的尊严意识,甚至不管它有无益处和欢乐,并且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终于开始怀着恐怖来看用强力终止生存,即使是悲惨而痛苦的生存——而我们的祖先却是问心无愧地采取这种强力终止的。 也应当记住,古代的道德行为准则对于所有的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人知道他对自己邻居的义务,但不是一切人都是他的邻居。这一点可以从人类关于杀人行为和野蛮行为的概念历史中明显地看出来。杀人行为未必被任何一个民族的法律都认为是本身犯罪;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自卫、战争、复仇、死刑和牺牲的情况下,它被认为是正当的或值得赞赏的行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族,不论它如何低级和残酷,会认为人们能够不分青红皂白地彼此相杀,因为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即使是荒野和林丛中的蒙昧社会也早已瓦解了。因此,所有的人都承认,任何一种法律都“不许杀人”,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种法律。看一看这种法律在那些残忍的部落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益的,这些部族把杀人行为单纯地赞许为勇敢的证明。例如,年轻的苏人部族的印第安人,在他没有杀过人之前,不许帽子上插羽毛,不能带有勇士或战士的称号。在没有“谋得羽毛”之前,他很难找到妻子。同样,加里曼丹岛的年轻的达雅克人,在他还没有砍下一颗人头以前,也不可能找到妻子。那种颅骨或带发头皮也一样,阿萨姆的那加人战士把它们带回家,就有权文身和跟那位或许整年地等待这种丑恶的结婚证明的妇女结婚。这并非必定要从敌人那里获得这种战利品,也可以借助最卑劣的背叛行为去获得,只要牺牲者不是杀人者本部族中的人就行。其实,这些苏人在自己的环境中认为杀人是犯罪;除了近亲复仇的事件以外,达雅克人对杀人行为进行惩处。这种事态实际上毫不矛盾,事实上全部解释就在于一个词:“部族”。部族制订自己的法律,不是根据杀人是好或是坏的抽象原则,而是为了保存自己。它的存在决定于在跟邻近部族的生死斗争中保卫自己。因此,它设立社会奖赏以证明战士在反抗敌人的战斗中的英勇精神,虽然在最后的蜕化日子里,它允许用取得任何一个老太婆的头,或取得一个隐伏在丛林中的倒霉的外部族人的头作为战利品,来卑鄙地履行这个手续。研究者在这种同部族人跟外部族人的单纯对立中,找到了关于通过全部古代历史而逐渐过渡到观点较为广泛而高尚的正义和非正义观念的关键。拉丁文hostis清楚地阐明了古代的事态;这个字的最初意义是“外人”,后来十分自然地过渡到“敌人”的意义上去。不只是在公开的战争中杀死敌人被认为是正义的,而且古代的法律还得出了这样的理论:杀死本部族的人和杀死外部族的人是犯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罪;同时,杀死奴隶仅仅是毁掉了私产。现在,殖民地的居民事实上不允许杀死黑皮肤的人或黑人,杀死黑人同杀死白色的本国人一样。人类生命神圣的观念,作为适用于一般人类的原则,在世界上传播得越来越广。 关于盗窃和抢掠的概念的历史,大致是在同样方向中发展的。在低级文明社会中,“不许偷盗”的法律是很著名的,但是这法律应用于同部族的人和朋友,而不应用于异地人和敌人。谈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阿特人(Ahts)时,斯普罗特(Sproat)指出,交给印第安人保存口头上的任何东西都将是十分安全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偷窃行为是通病。问题多少涉及到其他部族或白人的财产。但是他说,认为蒙昧人中的偷窃行为跟我们中间的这种行为是同样程度的犯罪,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和社会法律禁止对别的部族进行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在许多世纪中已经成为习惯。例如,旅行家们描述道,虽然非洲人在自己本部族范围内有关于财产的严格章程,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祖鲁人的军队,都可以偷偷地潜入远方村庄,杀死男人、妇女和儿童,留下被抢掠一空的环形村庄在地平线上冒起熊熊烈焰;而他们则高高兴兴地带着掠夺来的财物回到家中。古代尚武好战民族的法律,很好地表现在古代日耳曼人凯撒(Caesar)的名言中:“每一团体范围内的抢掠行为,都不要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而要作为一种操练青年和减少惰性的手段来称颂。”即使在新的文明时代,宣战可能仍然要使社会回到抢夺和掠获财物的早期阶段上去。但是在和平时期,财产的安全性也像生命一样越来越稳固可靠了。由于引渡的公约,罪犯们失去了从前那种逃往国外的可能性,而现在将落入他们罪行所在的那个国家的法官之手;引渡公约表明了现代把各个民族结合为承认其所有成员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社会倾向。 迄今为止,我们把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主要看作是人本身的道德感和舆论的道德感的结果。但是,在任何时候,都承认那些检查人的行为的较为有力的手段是必要的。在现代,遵守用罚款、监禁、鞭打甚至处死来惩罚罪犯的刑法的义务,被认为是普通的文明义务之一。但是这种制度也是逐渐产生的,并且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它是如何由原始事态发展起来的明显痕迹。在原始事态时,没有任何职业法官,任何刽子手,但是用自己的双手来进行审判和制裁,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审判和制裁的原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复仇。当野蛮生活中在疯狂的欲念影响下杀了人的时候,这种复仇权也就付诸行动。行使这种作为一种伟大社会力量的权利,可以在澳大利亚人中间很好地看到。正如乔治·格雷(Georye Grey)先生在他关于这件事的叙述中所说的,为最近的亲属之死而复仇,是最神圣的义务,土著被号召去完成这个义务。如果他忘记了这个义务而没有完成,那么任何一位老太婆都将会嘲笑他;如果他没有结婚,那么甚至连一个姑娘都不会同他讲话;如果他有妻子,那么她将抛弃他;他的母亲将悲叹、哭泣,因为她生了这样的败类儿子;他的父亲将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而他也就成了共同蔑视的对象。但是,如果杀人者消失不见了,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这类蒙昧地区和居民很少的地区,是很容易发生的。土著的习俗就接受了古代的学说,罪犯的整个家族都负有责任;所以当杀人的事成为众所周知的时候,特别是当真正的罪犯消失不见的时候,罪犯的亲属就要以逃跑来自救。甚至七周岁的儿童都知道,他们是否跟杀人者有亲戚关系,假如有,就要赶快躲藏起来。在这里我们得出了两个原则,任何一位研究者如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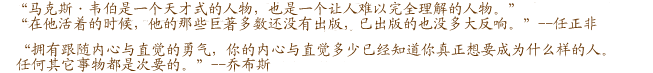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