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
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 [ E.B.泰勒] 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家庭——低级种族的道德——舆论和社会风俗——道德的提高——复仇和司法——战争——财产——法律——家庭的权利和义务——宗法的和军事的领袖——民族——社会阶级——统治 在每天发表在我们文明国家报纸上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中,常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如粗野狂暴,野蛮残酷。这两个词在一般会话中标志着这样一些行为:凶恶、暴虐、残忍。毫无疑问,较少文明的人——蒙昧人和野蛮人的生活,一般地说比我们是较为凶恶、暴虐和残忍的。但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还不完全在这一点上。正如前几章所证明的,蒙昧的和野蛮的部族常常或多或少明显表现着文化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也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在古代所经历的。而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常常从我们很难以别的方式猜想到的那个方面,来向我们说明我们的风俗和法律的意义和基础。不言而喻,这里也不可能引用哪怕是复杂的社会体系的一览表;所能做到的,就是给读者提供一些古代和现代生活中的指导性的社会原则。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人类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事其独自事业的一群个人而生存。社会总是由家庭或者是由从属于婚姻规约和亲手义务的亲缘所结成的经济单位组成的。但是,这些规约或义务极为多种多样。婚姻可能是永久的和暂时的一对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丈夫可能有若干妻子,和一个妻子可能有若干丈夫。在不文明的和古代的社会里,常常很难了解家庭的类型和它的关系。例如,对于我们来说,按照男系来确定家庭出身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儿子采用父名就一目了然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在两半球的低级文明阶段上,正如某种不言自明的事情那样,许多部族却恰恰具有相反的观念。在大多数的澳大利亚的部族中,孩子们都属于母族而不属于父族,以致在土著之间的战斗中,父与子经常作为当然敌人而相遇。领袖头衔常常按照帝王母系往下传。例如在纳切斯人(Natchez)中,这族人现在在路易斯安娜(Louisiana)地方有自己的太阳庙。但是,这种广为流传的由女系继承的习俗,尽管它是深深地发生在社会史中,也仍然被古代的文明民族所遗忘了,以致当希罗多德在采用母名并且只是按女系来追溯宗谱的百底亚人中见到这种习俗时,就以为这是某种使吕底亚人跟所有其他民族不同的特殊习俗。在蒙昧和野蛮的社会里,广泛流传一种麦克伦南称之为“异族婚姻”或“族外婚”的制度,这种制度禁止男人从本族内娶妻,否则,就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有时甚至被处以死刑。在澳大利亚部族中所看到的一种事实,跟通行的观念是一种奇怪的对比;蒙昧生活没有制度,那里的每一个男子应从另一族中娶妻,而这另一族同男方本族的关系可以说是妻族。在北美的易洛魁人( Iroquois)中,孩子采用母族或母族图腾的名字。例如,如果她是出自熊族,那么她的儿子也是熊族,照此他就不能跟熊族姑娘结婚,而应从鹿族或苍鹭族中娶妻。按男系确定出身的高级民族中,也有这类习俗。例如,在印度,婆罗门不能娶跟他同族的妻子(如他们所说的,她的“奶牛圈”);同样,中国男人不能娶跟他同姓的姑娘为妻。虽然在这里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家庭和部族的习俗加以充分讨论是极为困难,但是,有若干大可注意之点,读者应当注意。早期社会的婚姻是公民间的一种契约。例如,在尼加拉瓜的蒙昧狩猎部族中,想娶某一位姑娘为妻的青年,要杀死一只鹿并把它连同一堆薪柴放到那位姑娘父母的屋门旁,这个象征性的动作表示他愿意打猎和完成男人的工作。如果礼物被接受,那么婚姻就缔结了,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仪式。在具有高级文化的民族中,有较多形式上的许诺和带有宴会和亲属会聚的仪式;后来,也像其他重要日常生活事情一样,还请来神甫,以期得到神的福佑,并使婚礼神圣化。在举行这类仪式的地方,婚礼就变得跟野蛮时代的抢婚极为不同——如现在在巴西凶残的森林部族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抢婚,战士们对远方村庄进行袭击,用强力把妻子们带回家中。古代的传说十分熟悉这种习俗,如维尼亚民部族(Beniamin)的人们把希洛部族(Shiloh)节日里跳舞的女儿们捆了起来;或者在关于偷抢萨宾女人的著名罗马传说中——在以历史形式叙述抢妻的传说中;这种抢妻的活动作为纯粹仪式仍保留在罗马习俗中。这种抢妻活动在古代是如此通行的习俗,它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使现实中温和化的风俗已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种抢妻活动作为一种形式继续被保持了下来。这种活动在斯巴达人(Spartans )中已经转为这类状况;普鲁塔奇谈到斯巴达人时说,虽然婚姻实际上已经是家庭之间友好的契约,但是新郎的朋友们仍然还要演一场用强力抢新娘的“戏”。若干代以前,在威尔士人( Vales)中保留了同样的习俗。在那里,新郎和他的朋友们,骑在马上,武装得像在战时一样,把新娘带走。在爱尔兰甚至存在把枪投向新娘的护送者们的习俗,虽然在谁也伤不着的距离内——除非发生某种意外,如某位贵族霍斯(Hoath)失掉了一只眼睛。好像这种不幸情况也就结束了古代的这种奇怪的遗留。由于私有财产增加的结果,出现了买妻的习俗,例如,在祖鲁人中,未婚男子同姑娘的亲属们讲价钱,愿意为她出五头或十头公牛。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在我们那野蛮时期的祖先那里是一种习惯,正如从伊尼(Ine)的威尔土法律中所看到的那样,“假如一个人买一个妻子”等等。稍后些时候,喀奴特(Cnut)禁止买姑娘为妻,但是她自己要多少钱,丈夫可以给她多少钱。这样一来,某个时候作为新娘的身价而支付的钱,转变成了给她的嫁妆,这是法权史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当在较为粗野的社会状态下,寡妇跟已故丈夫的兄弟结婚的保障被停止时,这类的另一种保障就成为必需的了。 我们从婚姻开始谈起,因为家庭决定于婚姻,而家庭又是社会的全部稳定性的基础。所说的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中间较为野蛮的几类家庭联系的情况证明,从这几类家庭联系里,不可能期待那些设备完善的极好的家庭经济状态;文明社会如此多方面的良好性质和繁荣都应归功于这种家庭经济状态。但是,只要这些最野蛮的氏族不因败行和贫穷而彻底腐化,也不分化为各个部分,则某种家庭道德观念还是人所共知的,甚至也是在这些氏族中间实行的。它们的习俗——如果按照我们的观念来判断——是野蛮而残酷的;但是,眷恋和共同利益的家庭关系已经形成,在保护家庭时,母亲的忍耐温柔和父亲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之道德更务的基础,在他们对幼儿的一般日常关怀中,在兄弟姊妹彼此互相的依恋中,在相互的宽容态度中,在相互的准备帮助中,和在共同的相互信赖中,已经奠定了。这就从家庭传播到较为广阔的范围。部族的自然形成道路,就是由家庭或群体形成部族,这种群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扩大并分成许多经济单位,而这许多经济单位彼此仍然承认是亲属。这种亲族关系作为整个部族的关系,被所有的人都如此深刻地承认,甚至当各不同的部族发生混合的时候,只要一想为所有群体建立一种想象的关系,那么人们就常常虚构一位共同的祖先。因此,kindred(亲属关系)和kindness(爱护)是携手前进的——这两个同源的派生词,最恰当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主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从野蛮部落生活里能学习到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社会没有警察来维持秩序也行。显然,即使是地位最低下的人,不靠德国人所说的“Faustrecht”(拳头权),我们英国人所说的棍棒权(club-law)就不能生活。但强壮有力的蒙昧人不侵入自己那较弱小的邻人的茅屋,也不用带石镞的标枪投向茅屋的主人,而把他赶入森林以便强占这茅屋。没有站在普通权力之上的最有力的监督者,部族似应在一周之内就瓦解了;但是实际上,蒙昧部族继续存在了许多世纪。在食物不太缺乏,战争不太需要的良好环境里,低级的野蛮种族的生活在它的世代中可能是美好而幸福的。在哥伦布首次登陆的西印度群岛上,居住了一些被认为是全人类中最温和而善良的部族。旅行家尚伯克(Schomburgk)十分熟悉尚武好战的加勒比人的家庭生活,他描绘了他们那种令人想起人间乐园的风俗画,那时他们还没有被白人的劣行所败坏;他在他们中间看到了和平和快乐,以及淳朴的家庭的依恋,真挚的友谊和谢忱。他们不用夸大的语言,因而没有丧失其淳朴性。他说,文明世界不会再有机会学习他们的道德,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说他们是生活在这种道德之中。在新几内亚,荷兰研究家科普斯(Kops)提供了跟上述极为相似的对多里(Dory)澳洲土人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于水中木桩上的房子里,就像瑞士的古代湖上人那样。科普斯谈到了他们的温和,他们的习好真理和正义,谈到了他们那固定的道德法规;也谈到了他们对高龄人的尊敬和对儿童的爱护;谈到了他们产不锁门,因为他们认为偷盗是极大的犯罪,而这种行为极少遇到。在印度粗野的非印度部族中,英国的官吏们惊异地发现粗野山民和密林居民中的善良和愉快,以及他们言行中的极端诚实。例如,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先生提到南印度的一个地位低下的贫穷部族,农场主雇用他们来保护田地,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宁肯饿死,也不盲从受委托照管的地中偷一粒粮食。他们是如此诚实,所以,他们的字据会立刻解决哪怕是跟较富有的邻人的争吵,因为全都说:“库鲁巴人(Kurubas)永远说真话。”当然,关于加勒比人和巴布亚人的这些故事,证明了他们友爱的一面,然而跟他们战斗的人,则称他们为野蛮的、背信弃义的恶魔。但是在战斗中的残忍和狡诈,对他们来说却是正义的和值得赞扬的;我们在这里只研究他们和平的家庭生活。很明显,低级野蛮人可能是处在相当高的道德水平上,这一点尤其富有教益,这向我们证明了所谓自然道德。他们的宗教主要在于慰藉祖先的灵魂和自然的精灵,没有像在高级民族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强有力的道德影响。实质上,他们关于邻近人的行为极少受神的圣喻或害怕神罚的制约。这种行为多半决定于他们的生活安乐或不幸到何种程度。当战争的需要或不幸破坏了他们的安乐的时候,他们(也像那些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一样)的行为就变得较为残忍而自私。在缺乏任何安适的生活条件的蒙昧人群中,道德习惯总是低级的,他们为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以便在他们中能够发展较为温和的感情。此外,在人的低级部族和高级部族之间,还有那么一种差别:愚钝的野蛮人不具备能够升到文明人的高级道德观念的思维能力。蒙昧的森林人,忘记了昨天,也不关心明天,在自己的吊床里过着舒服口子。在他们的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上升到那种记忆和预见的功能上去,这种功能经常使我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来的生活情景,它还迫使我们在思想上投身处地,为近亲着想,而体验他们的高兴和悲伤。地球上发生的不幸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想象。如果醉汉能够看到,他当前如此嗜酒所感到的兴奋之后,在紧接的下一个小时之后将是不幸,那么这后面的不幸就可能遏制前面的嗜酒。在最暴怒的时刻,当人的思想上出现妇女围着满身鲜血的尸体痛哭的预见性画面的时候,剑常常反倒会插回鞘中去。低级种族的人如此地缺乏抵抗欲念和诱惑的先见之明,所以部族的道德稳定状态很容易被破坏,同时,他们愚蠢残酷,是由于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没有内心的同情,就像儿童对待动物很残酷,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这些动物的痛苦一样。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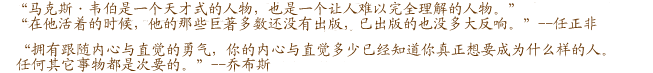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六章 社会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