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二章 文艺
| 优美的声音。图81画面上所描绘的祖鲁人的乐弓,装有一个指环,借指环沿弓弦的滑动来改变声调;还有一个空葫芦,作为共鸣器以增大弦所发出的微弱声音。在同一画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古代埃及的竖琴如何从这种简陋的乐弓发展而成。人们使木制的弓背内部变空.以代替它的弓弧和共鸣器,同时在它的横面拉紧几根不同长度的弦,这样它就成为竖琴了。
所有古代的竖琴——亚述的、波斯的以及古爱尔兰的——都是按这种设计制成的,但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结构的缺点在于:木背弯曲容易使弦失调。只有到了现代才变得完善:在竖琴上增加了一根前往,使整个琴架不可弯曲而很是坚固。看看这三种造型,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如何逐步发展的;不能设想,带前往的竖琴可能在别的一些形式坚琴之前发明,因为谁也不会如此愚蠢:人们一旦想出了前柱之后,再继续制造竖琴时不同时给它装上前柱。虽然现在竖琴制造得相当完善,但比起古代来,它仍然越来越丧失了从前在音乐艺术中的地位。它被由它产生的最新乐器所代替了。大钢琴的形式本身证明,这不是别的,而是这样的坚琴:它被斜装在琴箱上,它的弦现在不用手来选弹,而是用受键支配的小锤的敲击发声。这就是史前期战士弓弦发展的最后阶段。跳舞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轻率的娱乐。但是在文化的童年时期,舞蹈却饱含着热情和庄严的意义。蒙昧人和野蛮人用舞蹈作为自己的愉快和悲伤、热爱和暴怒的表现,甚至作为魔法和宗教的手段。巴西森林的印第安人,只有另外不多的刺激性的影响能够使他们萎靡的精神振奋;他们在月光下聚会的时候就活跃起来,开始跳舞。这些舞蹈各种各样:时而跳舞的人手中拿着抓哈板,在一、二、三的节拍下围着装有醉人烈酒的大陶罐跺脚;时而男人和妇女用舞蹈表现笨拙的求爱,他们排队移近,踏着好像原始的波兰舞的步子;时而涂饰的武装战土们跳起凶暴的战争舞,战士们唱着充满恐怖吼声的歌曲,一进一退成队地操练着步伐。我们本身也还遗留着足够的蒙昧人的本能,因而可以理解,澳大利亚人怎样通过在森林内篝火光火中的又跳又吼,就能使自己狂怒起来,准备参加第二天的战斗。但是文明化了的人按照他的观念就很难理解,野蛮人的舞蹈还能有巨大的作用。 蒙昧人认为,舞蹈具有某种十分现实的作用,因而他们期待着它对外在世界发生影响。例如,曼丹部落(Mandans)的印第安人在猎取水牛失败时,就吃水牛肉,举行卡特林( Catlin)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所叙述的仪式。每个印第安人都从家中拿出专门为这时用的假面具:这面具是用水牛头做的,有角,还有挂在后面的尾巴;大家都戴起来跳“水牛舞”。十个或十五个舞蹈者组成一个圆圈,敲着鼓同时击着呱哒板,唱着歌,还发出怒吼声。其中的一个人疲劳了,他就开始表演哑剧,模拟人们用弓箭把他射死,把皮剥下之后割成几块,同时,他便站到一旁去,把水牛头放在肩上,另一个准备着的人就站到退出舞蹈的人的位子上。舞蹈就这样不停地持续下去,一天一夜,有时两三周,最后,直到这些顽强的努力不能引来水牛,在大草原上没有出现任何畜群为止。 这类例子证明,在低级文化阶段上,人们跳舞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愿望。这全都说明,在古代宗教中,舞蹈何以成为祈祷仪式的主要行为之一。在埃及神殿中,宗教程序进行是伴有歌曲和舞蹈的。柏拉图说,由此看来,任何舞蹈或许都是宗教行为。实际上,古希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如此。在希腊,克利特岛人的合唱队踏着有节奏的步子唱着阿波罗的赞歌;在罗马,在每年的玛尔斯庆典上,萨利的祭司们唱着歌,打着板,沿着城市的大街跳舞。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在新的文明社会里,神圣的音乐较任何时候都更为繁荣,它大部分都摆脱了神圣的舞蹈。为了见识几乎是最古形式的舞蹈,旅行家就必须拜访印第安人的庙宇或去见西藏的喇嘛。在那里,他就可以看到,在蒙昧人的鼓和螺角号的音乐伴奏下,带着绘成动物形象的假面具的化装人,用舞蹈来驱除恶鬼或迎接新年。从基督教以前时期的英国宗教传到今天的这类仪式遗留,还可以在姑娘和男孩们围着圣约翰节之夜燃起的火所跳的舞蹈中,或在基督降诞节期的化装跳舞中看到。但是,即使是这些遗留,现在也正在灭绝之中。戴着带羽毛的有沿帽、穿着腓力三世时代少年侍从的艳服的教会歌唱者的舞蹈,至今仍在塞维里中央寺院主祭坛前表演,但现在也已是几乎从基督教中消失的极少数仪式残余之一了。在新世界里,舞蹈即使作为一种娱乐和优美的体操,也正在逐渐衰亡着。古代埃及的绘画证明,当时的专业舞蹈家,已经十分娴熟地掌握了大概在古代社会中已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艺术。令人想起古代绘画中的农村舞蹈的某种事物,还可以在除英国之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农村节日中看到。现代社会上的交际舞不但大大失去了艺术性,也失去了优美感。 在低级文化水平上,舞蹈和戏剧表演显然是不可分的。北美的“犬舞”和“熊舞”是模拟取笑的表演,它滑稽地忠实模仿动物爪的动作、在地上打滚和合乎动物其他习性的动作。不同的狩猎场面和战争场面,以同样的方法作为舞蹈的情节提供给野蛮人;而他们的妻子则留在家里,跳着模拟战斗的魔法舞,以便把力量和勇气赋予自己不在家的丈夫。历史家们把文明世界戏剧艺术的起源,归诸古代希腊的神圣舞蹈。在狄奥尼索斯的庆典上,酒神那充满神奇性的生活在舞蹈和歌曲中表现了出来,而悲剧和喜剧也就从这些庄严的颂歌和滑稽可笑的笑话中发生。在古典时期,戏剧艺术分成了若干分枝。哑剧保存了最古老的形式,其中舞蹈者用动作表现海格立斯和播种龙牙的卡德姆,同时在台下的合唱队伴随着演出,用歌声来讲述演出的内容。保留了古代哑剧风格残余的现代哑剧式的芭蕾舞,证明古代戏剧中戴着胡乱涂抹的假面具的神和英雄,想必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在希腊悲剧中,舞蹈者和合唱队的作用同演员的作用是分开的。演员在对话中每人单独用朗诵调讲话和歌唱。因此,演员已经获得了用充满热情和机敏的语言感动听众的可能性,同时他发音的声调和所伴随的手势,都能影响全体观众和听众的感情。希腊悲剧既已产生之后,就在艺术上迅速达到了高度水平。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是高级诗作的典范,最近模仿他们的作品像拉辛的《费德尔( Phedre)》,在舞台演出的过程中,当演员的天才能够表达出体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激情的时候,这些作品也能给人留下某些雄伟有力的印象。 最新的戏剧不只是跟中世纪宗教神秘剧的神圣表演有联系,同样也跟四世纪之前发生的文艺复兴有联系。看过锡腊库萨或图斯库隆(Tusculum)山坡上的古典戏场废墟之后,人们就可以了解,现代剧场的结构和各部分的名称都来自希腊。剧场,或观众席,都还保留着它那设计合理的马蹄形,当时的台前乐队席,或舞蹈席、歌唱席和一般合唱队演出席,现在则是乐队演奏席。现代演出的悲剧和喜剧的变化,与古代剧本的不同点,一部分是取消了非常牵强的庄严朗诵,而这种朗诵却为从前的演出所特有。当时,这些表演还仍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其登场人物都是神。在后来的剧作家手中——首先是在莎士比亚的手中,戏剧的性质变得较为人性化了,虽然这些戏剧仍然还继续描写最为紧急情况下的人性和最为激动人心时刻的生活。 实际上,现代的剧本并非必须严守自然,它们也可以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现代的舞台上,可以出现安琪儿或私人代替古典时代的神飞来飞去,他们通常是借助机械在空中飞行。在现代的喜剧中,出场人物的穿着和对话同日常生活可以那样接近。但是,在这里,听众仍然容许有另一种语言,虽然这种语言发音很大,是对“一边”说的,而不是说给站在旁边的出场人物听的;这就证明现代人并没有丧失其假设幻想的能力,而一切戏剧艺术就是建基于这种能力之上的。 建基在同一种假设幻想能力或想象力之上的,还有另外两种文艺——雕刻和绘画。它们的真正任务不在于精确地模仿现实。艺术家只是力图体现某种能够感动观赏者的思想。因此,用几道铅笔细线条绘出的讽刺画,或用木头粗略雕成的形象,较之工笔细描的肖像或陈列馆里的某种蜡像(这种蜡像是如此栩栩如生,以致参观者偶然碰它一下都要向它道歉),往往包含着更为巨大的真实的艺术性。 显然,绘画和雕刻是从现在儿童的绘画和雕刻的尝试中可看到的那种幼稚的萌芽中产生的。英国儿童们第一次尝试学画用的石板和板棚门,使我们想起了野蛮部落画人和动物、枪和小船的树皮块或兽皮块。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将成长起来共度过自己的一生,但他们并没有远离这个儿童阶段。有位乡村牧师几年前指导自己的信徒们,用木头雕刻各种不同的像是从事锻造或收获的劳动者的人形。他们制作出了粗笨得如此可笑的形象,而且跟野蛮部落的木偶十分相似,他们的作品可以保存下来作为童年状态雕刻的样本。但是,人类在顺利的情况下,特别是有长期闲暇的时候,从远古起就开始改进自己的艺术。特别是欧洲居住于洞穴中的人所作的动物形象的绘画和雕刻,带有如此之多的艺术迹象,以致有些研究家认为它们是现代的赝品。但是它们被确认为真品,并且在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而那些实际上为欺骗搜集家而制作的赝品,其特点正是缺乏那些蒙昧人所特有的那种艺术性,因为那些蒙昧人生活在北方鹿和古象中间,才善于掌握这些动物的形象和姿态。 涂饰艺术应该是十分自然地产生的,因为用炭、红土、红色和黄色的赭石涂绘自己身体的蒙昧人,自然也能用同样的染料开始涂抹自己雕刻出来的形象,或用它们来涂饰绘画的草图。去澳大利亚的旅行家们,由于在山洞里躲避暴风雨,有机会吃惊地看到粗陋的湿壁画艺术。壁画上描绘的是袋鼠、鸵鸟和土著们的舞蹈。在南非,布须曼人的洞穴被绘画覆盖着,画的有拿着弓箭的土著,有糖牛拉着的欧洲车,还有对土著来说如此可怕的荷兰布尔人的形象,他们带着宽缘帽,嘴上刁着烟斗。在一些像西部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这样的部族中,土著的雕刻家们的天才多半用在制作魔鬼像和神像上面,制作这种像是为了崇拜,是为了给无形体的神灵作寓居的住所。这样一来,野蛮人的偶像作为雕刻的不同阶段样品,既在艺术史上、又在宗教史上具有了相当的意义。 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部族中,艺术已经升到了最高阶段。实际上,埃及的雕刻与其说比以前、不如说比后来的若干世纪达到了它最好的典范的高度,因为较古时代的石雕充满了极大的自由和生气,而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Rameses)的巨像那冷酷而高傲的面容,体现了半专制君主、半神的东方暴君的最庄严的典型。在不列颠博物馆雕刻大厅中,可以看到埃及雕刻家们的初期学派,正处在通向希腊艺术完美性的途中,但还远没有到达。他们以其惯用的机械式的灵活技巧,用那种使今天的石匠见了都感到为难的最坚硬的花岗岩和云斑石切雕出巨大的人形,制作出成千上万的偶像。但是,这种跟传统有联系的艺术,不仅没有成为更加自由,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变成形式主义的了。他们善于把自己的平面分割成合乎规则的正方形,按尺度来制作头部和四肢,但是他们按成规所制定的形体,很少能达到希腊线条的优美程度。他们的纪念像在现代所以被认作珍品,并非因为它是艺术性的典范,而是由于它是古代历史的见证。 在同一座不列颠博物馆里,尼尼微装饰宫廷廷院中的雪花石膏的浅浮雕,给予人们以极鲜明的印象,好像人们就生活在亚述国,国王乘着自己的战车出发了;或者把自己的箭投进了自卫之狮;或者在礼仪之伞的下面行走,而那伞就撑在他的头上。我们看到了他们,那是一些士兵,乘着充气的兽皮划于在横渡河流;那又是一支突击分队,顺着阶梯登上要塞墙,同时,女墙上的弓发出的箭连续在射击他们;被处刺刑的俘虏,成排地在墙外面示众。但是在这类墙上,相称性并不重要,只有表现精神才是重要的。把箭头做得如此之大,两个就占了一整堵墙,亚述人并不觉得在艺术方面荒唐可笑。同样地,埃及人也没有感觉到他们那国王的巨人形象,给我们新时代人所造成的印象是多么滑稽可笑。这位国王跨过一半战场,一次就捉住十二个野蛮矮人,把他那有力的大刀一挥,就将他们的头颅都给砍掉了。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艺术法则否定了较古老部族的绘画,因为它们形式矫揉造作,安排布局很不自然。艺术的法则只在希腊发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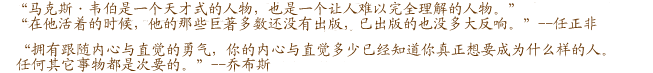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十二章 文艺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