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九章 技术(续)
| 的池塘里,常使水中含上素质,这类情况很容易使任何一个看到的蒙昧人受到启示。
还有一种蒙昧人采用的方法,就是用搭钩搭鱼,或用枪扎鱼。这种枪的边刃上有小齿或芒刺,为了增强效力,常常把枪的尖端分成若干带齿的小角。有人这样描写从事捕鱼的澳大利亚人:他横卧在树皮制的小划子上,把枪头放进水中,准备一声不响地刺穿进水去。更加精彩的是,他能在水下睁着眼睛,这样,不只水面的波纹不会妨碍他察看,光的折射也不会干扰他瞄准。由于光的折射,处在水面上的人要投准水下的某种物体,那是多么困难。蒙昧人也知道,黑夜降临之后,鱼就向亮处游去,于是就在火把的亮光下用搭钩搭捕鲑鱼,这种方法在苏格兰或挪威用得较少,但在整个美丽如画的温哥华岛上的印第安人中间,却都可以看到。许多原始部落以惊人的敏捷性用弓来射鱼,这可以看作是用搭钩搭捕鱼的变种。 钓鱼钩这种器材.并不是所有蒙昧部落都知道,但是有一些蒙昧部落知道。澳大利亚人用贝壳制成钓钩,也有的把大鹰的爪绑在木棍上用来捕鱼。和现代欧洲的钓鱼者相类似,古代埃及人坐在江河或池塘旁边,借助木棍和钓竿用青铜制的钓钩来捕鱼。希腊人利用人造的蝇虫来钓鱼,如果不用约竿,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用钓丝。一般地说,有趣极了,现代的钓鱼者在其方法方面,跟最原始人和古代人的方法相去不远:蒙昧人那种带有三四个锯齿状小角的捕鱼枪,和我们海员今天在用的称作搭鱼钓杆极为相似。只不过我们是用铁而不是用木头或鱼齿做头儿。美洲的捕鲸业者所使用的带索的鱼叉,也是这样。这种鱼叉带有一个装得不牢固的头儿,当穿入鲸鱼身上时,头儿就与柄脱离了,它只靠一根长绳和漂浮的木柄连结着。这种工具是从阿留申群岛人的带索鱼叉模仿来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头儿是铜制的而不是骨制的。我们现代的捕鱼者大规模地从事捕鱼,他们用轮船曳网,席卷整个海湾,但是,他们一面用网捕鱼,一面仍采用搭钩搭鱼和钓鱼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和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民族中见到的方法非常相似。 因此,人甚至当他像低级动物那样以采集野果和捉禽兽、捕鱼虾为生的时候,在其较为发达的智慧的指导下,已使用了获取这些食物的较为复杂的方法。过渡到下一个高级阶段的时候,他便开始为自己储备食物。 不能认为农业是一种十分艰巨的或非凡的发明。即使是最粗野的蒙昧人,当他熟悉了他所采集到的可食植物的性能以后,也应该清楚地知道,种籽或根,要是种在适当地点的土壤中,就必定会生长。因此,假如有如此之多的部落只限于采集自然给予的东西,而自己什么也不种植,那么,这并不能充分说明他们愚昧,而是说明了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说明风土恶劣,或者说明简直是懒惰。就连文化非常低的人,如果他们成年生活在一个地方,土壤和气候又都很良好,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开始种植东西,例如像巴西的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在自己的茅屋周围开垦了一块不大的林地,以便种上玉蜀黍、香蕉和草棉一类的植物。 认真研究一下世界上用来作食物的植物,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中,只有像椰子果或木菠萝这样不多的一些植物,是在野生的状态中繁殖的。它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在农业的影响下改变着形态。也有另一种情况,有可能找到某些处于野生状态的植物,但可证明,它是已经由人多少改良过的,像马铃薯就是这样,它被发现时是在智利的峭壁上野生的。只是,许多人工栽培的植物的起源,已经被遗忘了,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类植物就有属于那些通过耕种成为粮谷的可食用的禾本科植物,如小麦,大麦,裸麦,这些植物在现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这些禾本科植物由野生祖先变成为种植植物,显然早在有史时期到临之前,这也就是把农业的开端推移到还要古远的时期。 埃及和巴比伦连同它们的政府和部队、教堂和宫殿,证明农业的最初萌芽大概有多古远。要知道,只有在许多世纪农业的基础卜,才能形成这些人口众多的古代国家。植物,它们只要在某个地方一次受到培植,那就为自己在现世界开辟了从一个部族到另一个部族的道路。例如,美洲的欧洲侵略者们把玉米或玉蜀黍带进了欧洲。玉蜀黍从太古时代起就在整个美洲种植了,而现在,成为供给意大利农民每天午餐的玉米饭或粥。玉蜀黍现在也在日本培植,直至南非,它在南非是殖民的每天食物。 如果注意到原始部落如何耕地,那就可以知道关于发明农业工具的许多事情。类似澳大利亚人一样的流浪的蒙昧人,随身带着尖头的木棍,用来挖掘可食用的根,如图43中所描绘的。如果注意到植根和挖根过程之间的近似性,那么就可以较有把握地推测,开始耕地的部落,能够用先前只挖根的那些同样的木棍来耕地。实际上,作为简陋的农业工具的那些削尖了的木桩,也像在欧洲一样,在美洲也被发现。用形如宽头的枪矛、剑或桨那样带平刃的工具来挖掘,是一种改进。现代的铁锹就是这种形式。 最重要的工具——锄头,来自镐或斧。新喀里多尼亚人的木镐是用来作武器和种植薯蓣的工具,而非洲的铁刃斧,是装在狼牙棒上,要变成锄头,只要把刃横装就行了。奇怪的是,只能想象的那种最简陋的锄,是欧洲的。它甚至比北美印第安人妇女用来掘地种玉米的锄头还要简陋,它是用糜鹿的肩胛骨固定在木棍上构成的。这就是在图43中描绘的瑞典锄头。它是一根简单的粉枞木桩,下端有一个削尖了的突出的杈。在古代瑞典,就是用这个奇异的工具来耕地;一两代前,它在森林里的农民部落中还能够看到。瑞典的传说使我们了解到农业是如何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开始使用木锄是较为困难的。人们在地上拖曳它,用这种方法深耕出沟痕来。后来,工具就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有农夫的把手,和供拉这个原始犁的人用的杆或辕。以后,犁头镶上了铁头,最后,用双牛或双马代替人拉犁。 显然,锄头就是这样在到此之前的上千年中转化为犁。图44描绘的就是古代埃及的农业。在犁后面走的,是用一张奇怪的锄打碎土块的劳作者。那锄有个长长的弯木刃,用绳子缚在把手上。我们如果看看犁本身,就会发现,它是用同样的锄头构成,也是用绳子缚着。只是在这里,它是较为沉重的,并且装有两个供农夫用的把手,以便农夫能够驾御它,并把它紧压在地上,同时,由两头牛把它拖向前进。尼罗河流域曾是农业高度发展的最早区域之一,看了这里所引用的图画,我们几乎有权想象:这一伟大发明出生时我们在场,目睹了犁是如何产生的。给它装上沉重的金属犁头,赋予它以这样的形式,能使它像一把连续的梳子把草土块翻卷起来;把铧固定在前面,以便翻起前列的剖面;把所有的工具都装置在轮子上:所有这些改进,在罗马奴隶时期就已经闻名了。在现代,农夫已经不必跟着把手走了,而汽犁获得了比牛或马更加强大的动力。然而任何人,只要他看一看这一工具发展的较早阶段,就能够在最完善的现代犁中,认出拖曳在地上的原始的锄。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http://www.renleixue.com/制作 甚至现时还作为遗留而存在着一种野蛮时代的耕种荒地的方法。显然,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人,当他开始确立对当时只是到处采集野生根茎、干果和浆果的原始森林的控制权力时,是如何耕种的。这种原始的方法还是由哥伦布发现的。他在西印度群岛登陆以后,看到土著们正在清理某些地区,把灌木丛削除并就地烧掉。用这类简单的方法,不仅消灭森林,而且把烧剩的灰用作田地的肥料。迄今为止,这种现象在印度山区部落中间仍然还可以看到。这些部落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耕种若干年后,就转移到一块新的土地上。在瑞典,用火烧耕种土地的方法,不但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地方性的方法保留在传说中,而且直到现代,在偏僻的地方依然存在。这告诉我们,早期的部落,当它们移居欧洲时,它们的简陋农业也便随身带来。 看到现代的英国农场,我们不应当认为它是一下子完善起来的。现代农场经济的农业,在它的后面有一部漫长而完整的转变史。它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之一,就是多年以前这一时期,欧洲的大部分都首次以农村公社的方式来进行耕种。移民的部族占据一片空旷的土地,在这一部族的茅屋周围,拥有广阔的田野,这个部族像个大家庭一样,从一开始就共同清理和耕种这块土地。后来,经过多少年之后,把可耕地重新划分为家庭管理区段的习俗形式,但是全部农村田地仍然继续由整个公社来耕种。公社在这时还是袭用农村族长所确定的那种方式来工作。甚至在俄国,这种体制的遗迹经过了封建时代,在现时地主和佃农的时代,仍然还保留着。在许多英国伯爵的封地里,迄今依然可以看到大公社田的分界。这些公社田按长分为三段,每段横着又分成若干区,由各个家庭耕种。这三段田按照旧的三区轮种体制进行耕种:一段田休耕,同时,其他两段田种两种庄稼。 现在我们转到研究驯养动物的历史。驯养人所容易接近的动物,像鹦鹉和猴子,现在的原始林间民族仍在进行。他们在这类养驯的宠儿身上获得了特殊的乐趣。文化最落后的部落,为了看家和狩猎也饲养着狗。但是,人只有达到较高文化水平之后,才开始为了用作食物的目的而饲养和繁殖动物。在遥远的北方,在北方鹿的故乡,可以很好地按迹探求从狩猎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过渡。爱斯基摩人只是猎取北方鹿,然而西伯利亚的部落,就已经不只是猎取鹿,而且也驯养鹿。例如,通古斯人就住在自己的畜群旁边,他们牧养畜群不只是为了奶和肉,也为了用畜皮做衣服和帐篷,用筋做绳子,用骨和角做工具,在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的时候,鹿也就成了驾车和驮物的工具。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最简单的游牧生活的标本,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对众所周知的较发达的游牧部落作详细的描述,这些部落带着自己的帐篷,在中央亚细亚草原或阿拉伯沙漠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为自己的牛和羊、骆驼和马寻找牧场。 在流浪的狩猎生活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两者虽都是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但是它们的境遇极不相同。狩猎者过着设备极为简陋、极不舒适的生活,并且有时还遭受到饥饿生活的全部痛苦。对于逐水草而居的牧人来说,狩猎仅仅是生活的补充手段。他的畜群保障着他来日的生活。他有珍贵的牲畜,可以向城市居民换取武器和布匹。在他们的队伍中,有自己的铁匠,而他们的妇女则纺毛线,织毛布。把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就像上面刚提到过的我们祖先在古代欧洲农村公社所经历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就达到了安乐和舒适的更高阶段。在这里,在农村村边耕种过的田野附近,夏天在小丘上和属于公社的森林里,都放牧牲畜。森林里也有猎人猎取禽兽,同时,在靠近家门的地方还有公共的草地作为牧场;在冬季,把畜群赶进天幕下的畜栏里,有干草做保障。在像英国这样人口如此稠密的国家里,古代游牧生活的最后遗迹,从夏季停止驱赶畜群进山那个时候起,就消失了。 担心食物之外,保卫自己避免危险,是人的最重要的要求。蒙昧人不得不击退扑向他们的猛兽,他们也纵犬追捕并消灭它们。但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还是那种具有和他们相同的动物形态的生物。战争在最低级的文化水平上就已经开始了。人借助对付猛兽的狼牙棒、枪矛和弓来反对人。皮特- 里弗斯将军指出,人在战时是带着怎样的规律性,采用了从低级动物那里学会的方法,如他的武装模仿动物的角、爪、牙齿和尾针,直到包括尾针的毒。人还用模仿动物的皮和鳞的甲胄,来保护自己,而他的战争方法,像设伏兵和设立哨兵,首领在前面率部队进攻,发出威武的喊声进行战斗,也全是从鸟兽那里学来的。 上面我们已经研究了进攻性武器的最主要类别。给箭涂上毒药以加强其杀伤力,这在全世界的原始部落中都是常见的。例如,布须曼人把蛇毒和大戟汁混合在一起,而南美的蒙昧人,用长期斋戒来准备一种神秘的行动,在秘密的森林深处煮一种使人麻痹的毒箭。在那秘密的地方,对那个可怕的过程,妇女连一眼也不许观看。毒箭也闻名于古代社会,正如谈到奥德修斯的那几行诗所证明的。奥德修斯到厄皮尔去,是为了寻找涂他那青铜箭头的杀人毒药。 战士的甲胄如何起源于动物的天然铠甲,这是不言而喻的。动物的皮本身就可以用作甲胄。例如,在博物馆中就可看到用加里曼丹岛的熊皮制成的甲胄或用埃及的鳄鱼皮制作的胸甲。骑兵胸甲和销甲的名称本身证明,它们起初是由皮制成的。苏门答腊的布吉人(Bugis)制作胸甲,是把食蚁兽退鳞时所甩掉的小鳞片缀在树皮上,再把它们像甲片般一个叠一个地安放上,如同动物本身那样。萨尔马特人也用同样方法模仿动物的自然装备,他们把切割下来的马掌片叠放得像松果的鳞片一样,缝合在一起。采用金属以后,在上述这类技术的基础上就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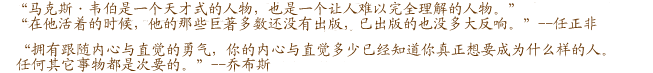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第九章 技术(续)所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