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 马克思人类学
来源 人类学阅读
浏览
发布时间 13/06/01
| dquo;,无疑会对马克思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许能够解释马克思为何会在晚年以相当的精力转向人类学。 19世纪中叶前后,东方几个主要大国如俄国、中国和印度等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正处于蜕变期,它们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正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东方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俄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尤为引起马克思的关注。 当时俄国《祖国纪事》杂志所刊发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中,把《资本论》一处对赫尔岑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的批判引申为马克思不同意赫尔岑主张的俄国人应当为自己的祖国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对他思想的严重曲解。由于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马克思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比较含糊地涉及了三个相关的原则问题:一是俄国究竟应走哪条发展道路?二是《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否适用于俄国?它是不是一切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究竟怎样认识俄国的农村公社? 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马克思在1877年11月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引述了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前途问题的看法,并说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非常重视地提到了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还说这位学者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 第129页。)。这说明,马克思约在1873 年以前就已注意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并开始认真地思考俄国的前途问题了。 为了能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此后,他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马克思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提法把米海洛夫斯基所质疑的第一个问题明确起来,并提高到原则高度来讨论,这其中包含着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同时对第二个问题亦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 1881年后,俄国的前途问题在俄国革命者中间的争论变得尖锐起来。俄国民意党中央和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动解放社”的主要成员查苏利奇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前景特别是对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学生,‘马克思主义者’”。“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多么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7页。)。 很显然,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个理论上的事情,而且还会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俄国革命家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到俄国的未来发展。因此,马克思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写回信。他一共起草了四稿。在前三稿中,马克思本想总结多年来的研究收获,在重点讨论农村公社问题的基础上对涉及俄国前途的几个重要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论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0―452页。)。但他后来改变了这种考虑,决定只以一种简要的方式作出答复:“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草稿中已对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这与他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加紧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特别是注意研究不同社会中的公社形式有关。1876年5月至6月,马克思把毛勒关于日耳曼公社史的著作作了详细的摘要。同年12月,他阅读了格・汉森、弗・德默里奇、乌蒂塞诺维奇及弗・卡尔德纳斯关于公社制度在塞尔维亚、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演变情况的著作。1879年夏天,马克思得到马・柯瓦列夫斯基送给他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后来认真阅读了该书,并写下了详细的读书笔记。但是,他仍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关于这些变化,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因而他在正式的复信中略去了那些关于农村公社的具体论述。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他于1881年后更加深入研究人类学的直接动因。事实上,马克思对摩尔根、梅恩和拉伯克等人著作的认真研读也正是在这以后进行的。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深层动因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唯物史观不仅需要解决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且还要弄清楚人类社会从何处来和如何来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用精神或观念来解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和宇宙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 页。)。根据这样一种思维罗辑,马克思从哲学走向了经济学,后来又从经济学转向了人类学。 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解决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他要弄清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化历程则需借助于人类学方面的知识。确切地说,唯物史观在确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人类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及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研读大量的人类学著述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并力求揭示出人类原生的公有制社会形态如何被后来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所取代,而最终又回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历史进化规律。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既是出于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对现实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俄国前途等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这两者不是截然分离而紧密相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升华和导引,后者则是对前者的验证与回应。 三、马克思人类学转向的现实意义与启迪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富思考的空间。如果只孤立地看待他的“人类学笔记”,或许它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如果将它放到他的整个理论的有机体系中去考察,进而联系我们当今的社会实际;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得到更多的理论启示。 (一)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东方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的认识。 在前面分析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动因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通过对当时人类学著作的认真研读,回答了俄国革命者及学者们普遍关心的俄国前途问题,即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具备着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东方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要么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艰难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么是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应该说, 这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主要指的是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或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条件。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通常是对立统一的。传统是现代的基础和原发点,现代则是传统的扬弃和发展。离开传统的现代化是难以存在的。没有传统的现代化,无异于一座没有基石的空中大厦。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出现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主要社会思潮。以往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它们对中国是在特定环境中被动卷入现代化问题的看法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对内忧外患条件下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合理转化问题上却存在着意见分歧。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我们或许能够从他对人类社会从何处来的思索中得到启发,进而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历史传统既不同于苏联东欧,更有别于欧美。中国“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影响着它的发展道路。从“来处”来思考、讨论它的“去处”,将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前途问题的探索,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单线进化论”和“多线进化论”问题颇有裨益。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它的现实国情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社会实现了有点类似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跳跃式变迁。但是,我国的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却遇到了失败和挫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些事实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能够在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跨越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但却不能跨越任何社会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领域中不能跨越的那些阶段。 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去理解,还必须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加以考察。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强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之中;同样地,我们充分肯定东方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发展道路,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东方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 (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对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nb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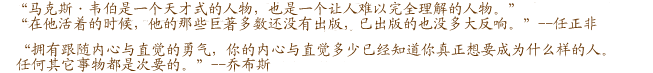
查看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转向及其现实意义所有评论